2024年4月14日,是中國考古界的悲傷一天。當晚,一些考古界人士開始在朋友圈轉發視頻,配以心碎的表情符號。視頻中,一位老者面目清瘦,眼窩深陷,而目光炯炯,嘴裏講著“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等概念。年歲似乎榨取了他所有多余的皮肉,剩下幹瘦筋骨,如葉芝的一句詩——“萎縮成真理”。
當天20時13分,著名考古學家、北京大學資深教授嚴文明逝世。

2015年,嚴文明在家中留影。攝影/韓建業
92歲的嚴文明,出生于1932年,從事考古71年。他擔任過北京大學考古學系主任、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去年被“第五屆世界考古論壇”授予終身成就獎,是第一位獲此殊榮的中國考古學家。北京大學稱,嚴文明是中國考古學界的一面旗幟。
比他小6歲、相識66年的考古學者、遼甯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譽所長郭大順說,嚴文明或許是中國考古學理論大師的最後一人。在他身後,將浩如煙海且越積越多的考古發現,提煉成言簡意赅的理論和見解,不知還有誰人。
和而不同
朋輩和學生們回憶起來,嚴文明從來都不是強勢的人。他對學生非常耐心,他的學生、首都師範大學曆史學院教授戴向明想起老師,一個畫面總是浮現出來。他1989年拜入嚴文明門下攻讀碩士學位時,嚴已經是系主任,事務繁忙,學生們有事請教,總是在夕陽西下時到傳達室,先給他家裏打個電話。嚴文明在家裏等他們,趁晚飯時間跟他們談談,談完飯都涼了。
嚴文明1958年剛留校當老師,同年郭大順正好進入北大考古系學習。郭大順記得,那時嚴文明就很溫和,直至晚年都依然如是。他的溫和下藏著細心,郭大順畢業後到遼甯工作,當時東北考古條件艱苦,嚴文明一直格外關心郭大順,東北需要幫助,他從不推辭。編寫牛河梁遺址考古報告時,郭大順請嚴文明審讀,嚴看得極其細致,意見寫了滿滿五頁紙。
嚴文明不愛爭執,但做學問總避免不了觀點分歧。嚴文明獨抒己見,從不跟風附和,卻從未跟人紅過臉。他有自己的處世之道。
對于老師蘇秉琦的一些觀點,嚴文明也不贊同。他坦誠說起過,比如蘇秉琦的區系類型理論將中國劃爲六個區系,他有不同意見。“但是我沒有一篇文章去駁斥,對老師不尊敬的,我絕對不會那樣做。”他在《何以中國》紀錄片攝制組的一次采訪中說。
戴向明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嚴文明寫自己的文章,表達自己的觀點,對于對立觀點,他不會專門批駁。因此,嚴文明的觀點之別,從未上升到“爭”。“和而不同。”戴向明說,他從嚴文明身上看到傳統文人的氣質。

嚴文明,2018年。攝影/肖夢涯
“他不會正面發起一個論戰,他後面會再寫一篇更深刻的文章,如果你仔細琢磨的話,會發現他會對學術上的一些爭論有所回應。”嚴文明的學生、中國人民大學曆史學院教授韓建業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比如1987年嚴發表的《中國史前文化的統一性和多樣性》,就是對一個重要問題的回答。
嚴文明和蘇秉琦的觀點之別,事關對中華文明起源的認識。一直以來,中原是中華文化中心的觀念根深蒂固,但上世紀80年代以來,全國各地進入新石器時代遺址大發現時期,尤其是長江下遊的良渚遺址、遼河流域的牛河梁遺址和長江中遊的石家河遺址等,動搖了中原中心論。蘇秉琦提出將全國分爲六大區系、各自都有文明起源的區系類型理論。這個觀點,後來被歸納爲“滿天星鬥”說。
嚴文明則始終對中華文明的統一性念茲在茲。他覺得即便是滿天星鬥,星座的亮度也不一樣,他也提出一個比喻:重瓣花朵。各個區系是花瓣,但還是有一個花心,那就是中原。他認爲早在史前時期,中國文化就基本形成中原爲核心,包括不同經濟文化類型和不同文化傳統的分層次聯系的重瓣花朵式格局。
蘇秉琦晚年出版《中國文明起源新探》,系統闡述了區系理論,此書由其學生郭大順協助整理成型。郭大順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很多人誤解蘇秉琦否認統一性,其實,區系類型的基礎就是有機的統一體。“他們觀點不完全一樣,但不是完全相反,要具體去看。”郭大順說。
嚴文明跟學生說過,不要因爲他是老師,就贊成他的意見,如果他錯了,學生們還是要反對。“學術是一步一步傳下來的,對老先生的觀點要有起碼的尊重,但也不要機械地去學,承前還要啓後,繼往還要開來。”嚴文明說。
去世前一年接受采訪,他仍感念地說,一生最重要的老師,就是蘇秉琦。
叩問大地
1943年,嚴文明在故鄉湖南華容上高小,不久傳來消息,日本侵略軍開進了華容城關。炮聲隆隆、硝煙彌漫中,老師上了都德的《最後一課》。故事講的是普法戰爭時,普魯士軍隊占領之前,法國老師給學生上的最後一節法文課。嚴文明聽得流淚。課後,學校疏散,回家途中,敵機已經飛到,在頭頂盤旋掃射。他把課本裝進陶罐,埋進後院一棵樹下,跟隨全家逃亡。
顛沛流離中,父親從未讓他放棄學業。學校恢複時,就送去上學,學校解散了,就到處讀私塾,跟著長輩學古文。那真是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的時代,他常常在路邊見到屍體。1953年,經曆了破碎的求學生涯後,終于考上北大,第一志願是物理,但最終被曆史系錄取。
一年後分專業時,考古教研室主任蘇秉琦找到他,動員他學考古專業,因爲考古是“文科中的理科”,也離不開科學。嚴文明聽從了蘇秉琦。此後他將用一生,叩問這片大地的前世。
雖然一生身處學院,但他也曾當過很多發掘項目的考古領隊,坐鎮一線指揮。他的考古發掘生涯最重要的履曆之一,當屬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
上世紀80年代,浙江余杭的良渚、遼甯建平的牛河梁、四川廣漢的三星堆、安徽含山的淩家灘等遺址,紛紛有驚人發現出土。天門的石家河也露出了些許苗頭。嚴文明推動北京大學考古系、湖北省博物館和荊州博物館三方聯合成立考古隊,1987年至1992年,他擔任石家河遺址考古總領隊,尋找長江中遊的新石器晚期高等級文明。

1987年,嚴文明觀察三星堆出土青銅面具。圖/北京大學新聞網
嚴文明最關心的問題是:石家河有沒有城?
有城,就有國。在連續發掘了多處遺址後,他派北大考古系兩位年輕教師趙輝、張弛,對遺址群又進行了一次全面勘探;1991年,他帶領隊員們再次找城。兩次調查確認,這裏果然有一座不太規則的長方形城址,總面積達120 萬平方米。此前發現的那些遺址,于是都有了具體身份:有的是宗教活動中心,有的是居民區,有的是墓地……石家河遺址群爲代表的長江中遊新石器晚期社會,已發展到相當高的文明程度。
2021年,石家河遺址入選中國“百年百大考古發現”。石家河遺址考古,至今有一個做法被津津樂道:考古隊設計了一整套完整的田野調查流程,成爲此後聚落調查工作的藍本。這次發掘,實則也是嚴文明聚落考古理念的實踐。所謂聚落考古,是以整個原始聚落爲研究對象,包括居住地點的環境、資源、經濟、建築、生活方式、社會組織、意識形態等,揭示其中的社會形態,有人類學的色彩。而此前中國考古,一直偏重器物和文化史。
“嚴先生的聚落考古研究,在中國是開創性的。”戴向明說,“《姜寨》那篇文章至今都是經典。”1981年,嚴文明發表《從姜寨早期村落布局探討其居民的社會組織結構》,以陝西臨潼姜寨這個新石器時代最完整的聚落遺址爲標本,實現他所構思的考古學理念之變。姜寨第一期發現了100多座房屋基址,嚴文明觀察布局和形制,將其分爲五群,每一群都有一座最大的房子,所有房子圍繞著中心廣場,房門都朝廣場而開,四周有墓地、圍溝、哨所、寨門,一座規整的原始社會公社重見天日。嚴文明推斷,這些房子屬于五個氏族,姜寨聚落由家族、氏族和胞族三級社會構成。
當時,他還沒有提到聚落考古這個詞。《姜寨》發表三年後,考古學者張光直從美國到中國講學,系統介紹北美聚落考古方法,這個概念在中國考古界風行起來。而嚴文明數年前就開始了實踐,領風氣之先。“如果僅就聚落考古研究理念和方法來說,(張光直對北美聚落考古的介紹)並不及早前《姜寨村落》在學理上的貢獻。”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主任張弛撰文指出。
考古中總有些無心插柳的奇遇。1976年,在陝西寶雞莊白遺址,西北大學考古隊挖出了一個西周窖藏坑,青銅器一個接一個出土。嚴文明去了一趟工地,看到一個裹滿泥土的大青銅盤,依稀有字。他慢慢剔除泥土,出現四個字:“曰古文王”。他一驚:這是著史的語氣。繼續剔下去,一個上午,他揭開了整篇青銅銘文,洋洋灑灑284字。這是西周考古中發現的最長的一篇文章,記載著西周曆史。
文章是一個叫“牆”的史官寫的,青銅盤遂被命名爲史牆盤。這並不是嚴文明最重要的一類考古發現,但充滿了傳奇性。那個上午,經由他的手,人們才知道了西周曆史中一些從未被知曉的細節。
群星閃耀時
嚴文明留校當老師時只有26歲,那是1958年。嚴文明接到一項任務,爲了建設馬克思主義考古學,學校要求突擊編寫一本《中國考古學》教材,他被安排編新石器時代部分。他初出茅廬,學問還沒學到多少,更匪夷所思的是,他要帶一批大二的學生一起編書,那些學生一天新石器時代考古都沒學過。
最後,書編出來了,但沒法用。這陣風過去後,他又獨自花了兩年時間,編寫出一本新石器時代考古講義。那是新中國第一本成體系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專著。此後,嚴文明的考古研究和教學一直集中在新石器時代,這也是文明起源和形成的重要時期,他的關注點,將最終落腳于此。
1980年代,考古學系主任宿白對副主任嚴文明說起一個想法。各時代考古學一直分時段教學,老師們就像鐵路警察,一人守一段,但學生的整體認識被割裂了,宿白希望新開一門中國考古學通論。嚴文明很同意,問宿白,誰來教?宿白說,恐怕只好我們兩個人擡,以後再由年輕人接棒。開課後,嚴文明教上段,到春秋戰國爲止;宿白教下段,從秦漢到元代。
這門課成爲很多學生記憶深刻的經典課程。多年以後,1987年入學的韓建業回憶道:“嚴文明先生講上半部分,講得邏輯清晰,深入淺出。宿白先生講下半部分,邊講邊寫邊畫,速度很快,字圖俱佳,我可以把他說的幾乎每個字都記下來。”
除了留在考古學史中的那些經典理論和著作,身爲教師,課程也是嚴文明的作品。
從1962年開始講授“新石器時代考古”課程,到與宿白合作的“中國考古學通論”,1990年,他又專爲本科生開設“考古學導論”。考古發現和資料不斷增多,講義也越來越厚,嚴文明的講義變成《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學初階》《走向21世紀的考古學》等著作。這些課程,實際上是中國考古學學科體系建設的重要組成,尤其是新石器時代考古學科,基本就在他的這些課程中創立。
去世後的訃告中,北京大學總結了他在考古學教育中貢獻:北京大學考古學學科和人才培養體系的主要設計者和領導者,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學科體系的創建者,中國考古學科發展的引領者,中國考古學與文化遺産保護思想家和卓越的考古學教育家。
本世紀到來前,中國考古學界曾群星閃耀。
在北大考古文博系,數十年來,幾位著名學者各自鎮守一方。呂遵谔教舊石器時代,嚴文明教新石器時代,鄒衡領銜商周考古,俞偉超坐鎮秦漢考古,魏晉至宋元考古由宿白執掌,再往前,則有裴文中、安志敏、郭寶鈞、蘇秉琦等老先生開宗立派,再加上社科院考古所的夏鼐、尹達、王仲殊、徐蘋芳等老學者,他們奠定了中國考古學理論和方法。
這些大師級學者,往往有撥雲見日的功力,理論總結和概括能力極強。如今,學科分類越來越細,廣泛占有資料,再高度提煉概括,難度越來越高。而資料越多越需要總結,否則如入密林,一葉障目。郭大順說,某種程度上,嚴文明是“最後一人”——既是這批理論奠基者中最後走的一個,可能也是最後一位具有高度理論總結能力的學問家。

2006年,嚴文明(中)與考古學者戴向明(左)、張弛(右)在山西垣曲國博考古工作站。圖/戴向明提供
“以後越來越困難,但又必須得有這樣的概括。應該通過紀念嚴先生,來好好總結老先生們形成的體系,考慮下一步怎麽發展。”郭大順說,跟很多其他學院裏的學者一樣,嚴文明將大多數精力用在了課堂和指導各地發掘,著述並不算多。
捅破窗戶紙
說起嚴文明的理論功力,一個典型例子是1981年發表的《龍山文化和龍山時代》。在這篇文章裏,他爲中國考古學留下了“龍山時代”這個命名。
龍山文化得名于上世紀30年代,山東龍山出土城子崖遺址,被命名爲龍山文化,主要特征和標志物是黑灰色的陶器。後來,同時期發現黑陶的考古遺址越來越多,比照山東的龍山文化,各地陸續命名爲中原龍山文化、陝西龍山文化、湖北龍山文化等,造成了混亂。
怎麽理解這些距今4000年前後的龍山文化呢?嚴文明在這篇文章中,提出“龍山時代”概念,整體指稱那個時代在地域和特征上都有緊密聯系的文化。在龍山時代,中華大地從野蠻過渡到文明,它上接仰韶時代,下接早期青銅時代,與中國曆史中的夏商周貫通。從此,對中國史前時期的描繪變得異常清晰。
在郭大順眼中,這正是嚴文明概括能力的一次體現。“它是一個高度的概括和命名,結束了各方各說各的、亂七八糟的狀態,”郭大順說,“他就是有這種綜合的能力。”
另一個例子,嚴文明晚期對中華文明起源的格局,又提出“三系統”的理論。但在著名的“重瓣花朵”掩映之下,這個理論沒有受到太多重視。嚴文明認爲,中國新石器時代可以分爲中原、東南、東北三個系統,劃分依據是社會經濟發展,主要文化特征是鬲、鼎和筒形罐,鬲起源于中原,鼎起源于東南,筒形罐起源于東北。三大系統既獨立發展,又有密切聯系。
“三系統”想法從80年代萌芽,90年代提出,又經多次修改,2019年收錄在文集中。不過,文章最終沒有寫完,郭大順說,最後一部分只有提綱,但這個理論同樣值得重視。
嚴文明對每一個關注過的領域,幾乎都做出過經典的理論貢獻。最早,他研究仰韶文化,全面總結仰韶文化的分期、分區和劃分類型等,出版的《仰韶文化研究》是國內研究仰韶文化的唯一一部個人專著。後來,他研究農業起源,從理論上解釋爲何稻作起源于長江流域。
後來人們常說,建立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分期和譜系框架,嚴文明有重大貢獻,也是他一生致力的方向。這是一項恢弘的工作,要爲幾千年曆史理出脈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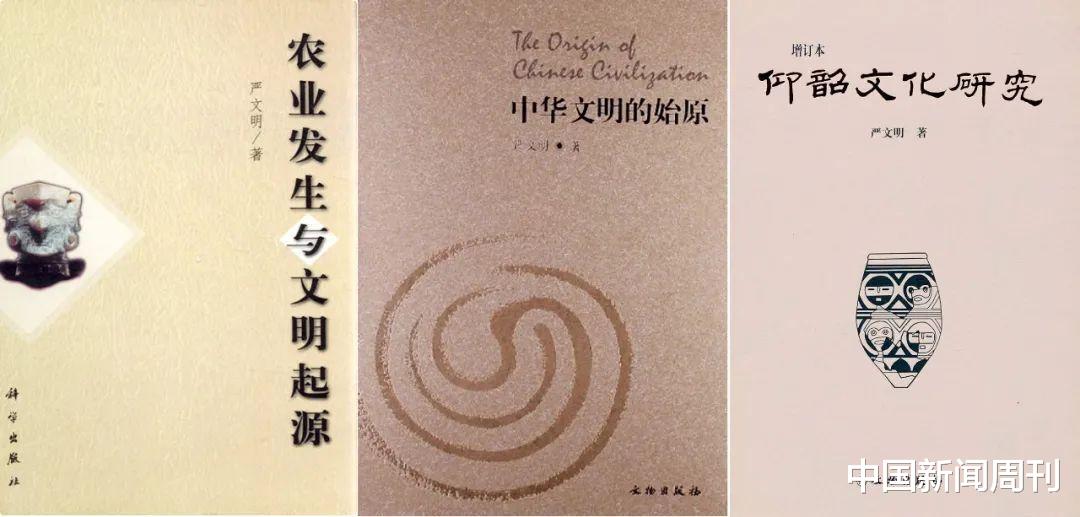
嚴文明代表著作。
“嚴先生一直在思考大問題,”韓建業說,做新石器時代考古的人很多,但能把全國範圍內整個新石器時代的東西說得比較清楚、通暢的人極少,“嚴先生就是其中最傑出的一個”。日本學者宮本一夫曾在嚴文明門下學習,他評價說,嚴文明在運用理論、總結歸納方面非常優秀,“至今無人能與其匹敵”。
2007年,戴向明准備啓動山西绛縣周家莊遺址考古。周家莊遺址所在的晉南是古代中原核心區域。他向嚴文明彙報了計劃,嚴突然提醒他注意一個生僻的話題——戎狄。一般認爲,西至甘肅、青海地區,北至黃土高原,才是戎狄活動的區域。這趟中原腹地的考古,爲什麽要關注戎狄?那時戴向明還不明白。
此後幾年,山西、陝西等地陸續有一些重大發現。2012年,陝西神木發現石峁古城,那是一處新石器時代晚期北方民族建立的大型城址。近年,陝西清澗的寨溝發現了規模媲美于商王陵的宏大晚商陵墓,當屬戎狄活動區域。這些發現都表明,戎狄的發展程度和活躍區域,都遠超傳統認知。“嚴先生那麽早就意識到,晉南與相鄰的晉陝高原有密切關系。他可能一直在思考中原和少數民族的互動,認爲晉南也是一個交融的地區。”戴向明對《中國新聞周刊》說。當這些發現清晰地擺在面前時,他才領悟嚴文明當初的提醒。
而嚴文明意識到這一點時,這些重要遺址還在沉睡,只有一些零星發現。“這是一種‘捅破窗戶紙’的能力,”戴向明說,“沒有那麽深厚的學術積累,沒有非凡的洞察力,就捅不透。”
嚴文明曾解釋,他學過哲學,哲學上說,認識是從局部實踐中來,最後進行概括,從低層次概括再到高層次概括。每種概括又可以回到實踐檢驗,總是這麽來來回回。所以他特別強調實際工作,總結的概念和認識要拿到實踐中檢驗,“如果經不起檢驗,盡管說得好像很圓滿,實際上你自己都不相信”。
如果學術世界是一座金字塔,嚴文明就是站在塔尖的那一類人,所有的材料、事實、進展都向塔尖彙聚,最終由他破解謎題。
考古資料再多,最終目的是一致的,嚴文明始終沒有忘記。這或許是他總能總結出大理論的原因。自始至終,嚴文明對中國考古學根本目標的認識基本沒變,就是建立國史——通過考古資料,建立可靠的中國曆史,認識中華文明。
中華文明是什麽?嚴文明將目光投向渺遠又蒼茫、神秘又晦暗的上古歲月,陶片、玉器和斷壁殘垣裏,有先民要說的話。他不斷用這些實物的證據逼近謎底。從抗戰烽火中走過,品嘗過亡國恐懼的嚴文明,用一輩子去探索和解釋中華文明。
去年夏天,紀錄片《何以中國》攝制組采訪他,問起中國的起源。“沒有任何外力,可以把中華文明推倒,”他揮了揮手,斬釘截鐵地說,“不可能。”
參考資料:《耕耘記——流水年華》,嚴文明著;《20世紀中國知名科學家學術成就概覽之嚴文明》,韓建業撰文
發于2024.4.29總第1138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大師嚴文明:用一生破譯中華文明
記者:倪偉
編輯:楊時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