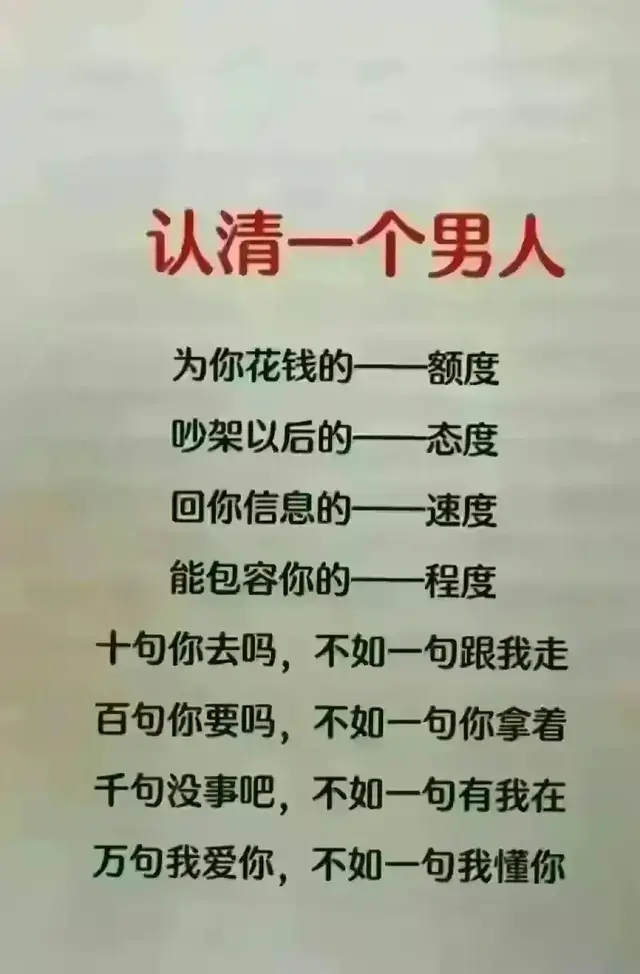2002年6月17日清晨,一位早起的小夥子在商丘市睢陽區中醫院門診部發現了一塊人的軀幹。緊接著,又有人在梁園區福源集團北街侯莊村發現了一截人的大腿。
現場勘查後,法醫說,屍塊是一個男人的軀幹,背部有24處刀傷,年齡在40歲至50歲之間,死亡時間在24小時以上,解屍的工具是刀和鋸。其他就再沒有一丁點兒線索。
說實在的,把商丘的曆史往上翻個幾十年,也找不到如此惡劣的碎屍案件。手段殘忍自不必說,凶殘的犯罪分子還敢把屍塊抛到市區最繁華的地帶。想想,這事兒能傳多快吧。
商丘市領導下了指示,這起案件手段殘忍,抛屍地點又在繁華地段,各界幹部群衆反應強烈,社會影響極大,請公安機關迅速破案。
屍塊不可能告訴我們更多的東西,于是“6·17”專案組只好用起了“笨”辦法——排查。這法子雖說是跟錢和大量警力過不去,可還是很管用的。

羅雲良的失蹤就是通過排查發現的。他已經失蹤兩天一夜,可他的家屬卻沒有報案。專案組聽說這事兒以後,立馬找到羅的家屬了解情況,羅的家屬開始還不太願意配合。他們說羅雲良怎麽著也是個領導幹部,事兒傳出去了不好聽。不過專案組還是知道了羅雲良是睢陽區公路局副局長,時年48歲。盡管專案組實在不願意給這些已經失蹤親人的人再增添什麽痛苦,但通過血型、身體特征等條件的對比,最終證實了被殺的人就是羅雲良。
很快,從羅的一位密友張某口中,偵查員了解到:6月15日下午,羅雲良曾接到一名叫曉雲的姑娘的電話,曉雲說有好事讓羅去一趟。張還讓羅不要去,羅卻說:去了還能把我害了?張說,曉雲是個坐台小姐。
曉雲是啥樣子?誰還和曉雲認識?這成了最需要破解的謎團。
偵查員們分頭去找羅雲良的故友新朋調查走訪。這不是什麽難事,很快,就圈定了人選。其中就有一位某區某局副局長李劍,羅雲良的鐵哥兒們。李劍顯然反感這種問與被問的場面,因爲他現在是被問者。盡管這只是“詢問”而不是“訊問”。
“對羅的失蹤你有什麽想法嗎?”
“應該不會出啥事吧。”
“聽說你跟曉雲關系不錯。”
“曉雲?什麽曉雲?讓我想想。哦,想起來了,與朋友吃飯時見過一兩次,其他就沒啥了。”
不過幾個鍾頭,偵查員就證實了李劍說的全是假話。
這回,李副局長滿頭大汗地承認了自己和曉雲的情人關系。此外,他還承認了羅失蹤那天下午他和曉雲通過四次電話的情況。
李劍說,當時他就問了羅失蹤的事,但曉雲說不知道。李劍還說出了曉雲的住處的大致方位。
專案組民警終于在淩晨3點時,從市電視台對面的一幢單元樓上找到了作案現場,還找到了用塑料袋裝著、水泥封著的頭和余下的屍塊,還在一口新鍋裏發現了被煮過的兩條殘臂。

專案組順藤摸瓜,就是順著曉雲和李劍最後那幾次通話的“藤”,“摸”到了電話機主,然後又找到曉雲的姐姐。這時,民警們才知道曉雲的真名叫榮穩。她殺人後在姐姐這兒住了一晚,告訴了姐姐殺人的事。她還怕過多連累姐姐,一早就不辭而別。
已經被妹妹連累苦了的姐姐告訴偵查員,她有可能躲在姥姥家。她果真在。偵查員們沖進去的時候,榮穩正准備從陽台上跳下去。偵查員抓住她的胳膊,她還是拼命掙紮著往下跳,但很快就嘤嘤地哭了。
榮穩交代了殺人的事兒,而且交代了和她一起殺人的同夥陳建東。
榮穩說,22歲的她已闖蕩世界5年了。榮穩生長在一個很普通的工人家庭。在她小的時候,工人手中的鐵飯碗還是很讓人羨慕的,于是她的父母就給了她很安逸的生活。也許是漂亮和安逸多少壓制了她的上進心吧,初中畢業後,榮穩沒能考上任何一所學校,可這對她不是太大的打擊,因爲就是考不上學,她也用不著回農村“打牛腿”,她是城裏人。

果然,1997年的夏天,她在家只閑了半年,她的爹就讓她接替自己去了那個養活他們家許多年的老工廠。但誰也沒有想到,榮穩剛捧住這個飯碗,這個飯碗就碎了。更不幸的是,她的父母還都有了病。在家閑著的日子很煩。病多錢少的父母也沒法再給榮穩舒心的日子。心很強的她就做出一個讓親朋都萬分驚訝的舉動,一個人在外租房,闖蕩世界去了。
可以想像,沒有知識又沒有一技之長的榮穩會在這個社會遇到什麽。她先後打過工,做過小生意,不是被騙就是賠得血本無歸。有段時間,最基本的吃飯穿衣都成了問題。榮穩像片浮萍整日漂蕩在這個生她養她卻又一下子拒絕了她的城市,尋找著可以棲身、可以掙錢的所在。本事都是逼出來的。榮穩很快發現了自己還有一種可以開發利用的資源,就是自己的漂亮。經過一番琢磨,她發現美容美發是個不錯的行當。
1998年底,她請了倆“小姐”,開了家小美容店,經營起自己的“事業”來。不過,作爲老板,榮穩還是有不出賣自己的底線。當然,這種底線只保持在遇到李劍之前。李劍就是在一次“消遣”的時候偶然看到榮穩的。

才18歲的榮穩怎麽看都讓他著迷。他開始成爲榮穩小店的常客,他還借著自己的“影響力“在生意、生活上給了榮穩許多關照,替她擺平了好多工商、稅務方面的麻煩。說實在的,李劍的這些舉動咋能不讓處在社會底層、整天承受著巨大壓力的榮穩感激萬分。就這樣,一半感謝,一半報恩,榮穩投向了年齡幾乎比她大一倍的李劍的懷抱。換句話說,榮穩就像一只小鳥找到了一棵可以棲身的大樹。在樹上,風雨都奈何她不得。
可是榮穩想得有點兒太簡單了。雖說李劍給她租了套好房子,配上了手機還報銷話費,還經常開車帶著她到大城市買衣服、添首飾,去一些百姓不敢去的高檔地方,可榮穩還是不快樂。因爲李劍不會給榮穩真正的愛情或者說是一種名分。他們之間就只能是偷偷摸摸,榮穩只能躲藏在黑暗的角落。慢慢地,榮穩變得很苦悶。
審訊時她對審訊員說,我不甘心就這樣過一輩子。後來,我連美容院都沒心再幹下去。我心裏憋屈得難受,還學會了吸煙、喝酒。那段時間我想,再不出去幹點啥,自己肯定會瘋。
她想遠離這一成不變的生活,也想尋找更多的金錢甚至是愛情。榮穩決定去山東菏澤市去闖蕩。菏澤離商丘不遠,而且在那兒做事會很自由自在,不用擔心親戚朋友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麽。榮穩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李劍,李劍沒有阻攔。其實他也不想阻攔,他的身邊並不缺少女人。榮穩到了菏澤以後,很快就到了一家當地挺有名氣的歌舞廳裏坐了台,她也只能去坐台。

後來,榮穩對偵查員說,要是不去菏澤,要是不去坐台,要是不去認識陳建東,這個殺人的事兒就不會有。可這一切還是發生了,因爲這些就是當時榮穩追求的自由和幸福。追求幸福並沒有錯,誰不想過得好一點!
本案的另外一個凶手,菏澤的陳建東,是專案組在抓住榮穩後的第三天淩晨抓住的。偵查員沖上去摁住他的時候,他身上的汗多得很,民警的手直打滑。當時,只穿著褲頭的陳建東在地上渾身顫抖著說,你們咋來恁快?你們要是再晚來幾個鍾頭,我就會坐上去上海的火車啦。
這也許就是23歲的陳建東的人生定數吧,就像他和榮穩的相識一樣。
被押回商丘的時候,陳榮穩其人建東已經沒那麽緊張了,只是臉上還挂著沮喪的神情。到了商丘,他說能不能讓他再見見榮穩。這一對見了面的“情人”的表情很複雜,說不來是激動還是難過。隨後,陳建東就交待了和榮穩一起殺害羅雲良的犯罪過程。交代完他說了一句話:“我也不知道自己咋就那麽喜歡她。”

陳建東也算是個不幸的人。他的老家是在山東菏澤,可他卻在江西長大。大了,父母卻都沒了。一個人老在外呆著也不是個事兒,他就回了老家,不管怎麽說,老家總還有親戚朋友。靠著親朋,陳建東在菏澤市開了一家賣汽車蓄電池的小店,雖說是慘淡經營但也能保證衣食。陳建東說自己曾經很寂寞,是情感上的寂寞,那種寂寞是最折磨人的。他說自己雖然老家是在菏澤,可說吃大米,這在別人眼中就是有什麽出衆之處,人也有些歡他。他只能把目光投向那。2001年9月,在他常去的這家歌舞廳坐台的榮穩。
跳舞。交談。抽煙。喝酒。吃飯。唱歌。別人在這種地方交往的過程,他們倆也都經曆了一遍。這一遍下來,兩個同是外鄉人的男女就找到同病相憐的感覺。倆人開始無話不談,一日不見如隔三秋了。很快,他們同居在一起,過起了快活日子。
讓榮穩說起來,陳建東是個很癡情的人。他對榮穩很好,甚至不嫌棄她是個坐台小姐,因爲榮穩告訴他這都是生活給逼的;還因爲榮穩會用女人的溫柔滋潤他,讓他不再覺得寂寞。他們還真過了一段很美好很浪漫的日子。普通百姓家裏該有的在這個“家“裏都有,從物質到精神的。比如榮穩一回到住處,就會有廚藝不錯的陳建東留好的熱飯菜;比如榮穩的胃病犯了,就會有陳建東來盡心伺候;比如他倆還經常扯著手一起逛街、遊玩。
後來,榮穩幹脆就不坐台了,反正陳建東還是有點錢,能養活得住她。有一天,陳建東甚至還和榮穩商量了結婚的事。

可這個世界真的有太多變數。
2002年4月的一天早上,榮穩跑了。爲什麽要跑?陳建東說真的弄不明白,自己那麽疼她,差不多把心都掏給她了,可只是吵了一小架,她就偷偷跑了,再也不回來。榮穩只是說吵架的那天有點煩,就是想走。他們說不清自己的事,可專案組卻能幫他們理出一點頭緒。
榮穩在陳建東那兒住著的時候,還是沒有忘記和李劍聯系。時間長了,這就不可能不露一點馬腳。陳建東就起了疑心,開始處處留心她的行動。當然,榮穩也不是沒想過和陳建東結婚,只是她不敢,怕李劍也怕約束。她也知道,這樣下去總歸不是個辦法。那天,她發現陳建東偷偷翻了她的包,于是她就有了一個合適的借口,離開了陳建東。
回到商丘的榮穩又成了自由之身。她把自己回來的消息告訴了李劍。回商丘沒幾天,不甘寂寞的榮穩就又重操舊業,在一家李劍他們基本不去的歌舞廳偷偷當起了坐台小姐。只是,這一切她都瞞著李劍。她在李劍的心目中一直是位純潔的女孩。
榮穩說,就因爲羅雲良發現自己是個坐台小姐,所以就只能殺了他。這就是本案的作案動機,簡單得有點讓人匪夷所思。

那是5月份的一天晚上,榮穩正在舞廳坐台的時候,突然有個人拉住她說,曉雲,你咋幹這個?這個人就是羅雲良。榮穩是很了解羅雲良還有他的朋友們的。在常人的眼中,羅雲良、李劍他們無疑是很成功的男人。這個圈子裏的人還都有一個共識,就是認爲女人一旦跟了他們,就不能再跟別人,不能做對不起他們的事。在強勢的他們的邏輯中,這一點兒都不奇怪。這就可以解釋羅雲良在那種地方遇到榮穩時的驚訝了。
他上前問榮穩,榮有點結巴地說,羅……羅哥,我沒幹啥。羅雲良又說,你在坐台。這回,榮穩沒有辯解。羅雲良就走了,可他不知道這些看似平淡的話會給對方帶來多大的恐懼,同時會給自己帶來怎樣的厄運。
榮穩害怕極了。她清楚,李劍知道以後,會斷了給自己的一切經濟“援助”,甚至還會狠揍她一頓。她還想到了患偏癱後遺症的父親、患心髒病的母親知道此事後的後果。恐懼有時候會化爲一種力量。
榮穩就把它化成了殺人的力量。
6月15日,她請來了陳建東,告訴他要殺個人,這個已經癡迷于她的男人則成了一台聽命于她的機器。上午,倆人一起采購了作案工具。下午,榮穩把電話打給了羅雲良:羅哥,你來我這兒一趟吧。羅說,啥事兒?榮說,你來嘛,有好事兒。羅雲良就來了,來的時候還抓起1300元錢塞進了自己的皮包。
榮穩是穿著胸罩、褲頭迎接羅哥的。因此羅絲毫沒有察覺從背後飛到脖子上的一根很結實的尼龍繩。實在不敢想象榮穩對羅雲良到底有多恨,她不僅一口氣紮了他24刀,還一邊喝著啤酒一邊拿著電鋸把他分成了11塊。

榮穩毀滅的絕不僅僅是羅雲良一個人。一同毀掉的還有她、她的親人、陳建東,當然還有李劍。
就是這樣一個沒有什麽曲折的案件,卻有著很悲劇的結果。案件的開始應該只是羅雲良的那幾句話,可他近于平淡的話只能算做一點火星。可怕的是,這點火星卻點燃了身處弱勢群體中榮穩埋藏在心底的對生活的極度恐懼,對自身的極度自卑和心靈上的極度壓抑。點燃的結果是一場核爆,摧毀了她身邊的一切。而李劍、羅雲良這些強勢群體,只知道把自己的欲望不加限制地施加、宣泄,而且大都是建立在別人痛苦之上的宣泄,卻不知這就像那玩火者一樣,雖然暫時有些火辣辣地刺激,卻總有一天會引火燒身。
說起來也真替案子裏的人們可惜,要是沒有這些事,他們每個人都應該是很幸福地生活著,仍舊很快樂地進行著欲望的遊戲與碰撞……
(因可理解原因,文內人物除罪犯外,其余均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