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衆多都市劇濃墨重彩地描寫情感糾葛的當下,一部短劇悄然亮相。
情節如溪水般細膩,台詞似涓涓細流,輕輕觸及觀衆的心弦。
片中展現的新疆阿勒泰美好閃光的日常生活,令人向往。
作爲國內首部散文影視化成功改編的作品,《我的阿勒泰》的成功也改變了散文作品弱情節不宜改編成電視劇的長期誤解。

當下,由馬伊琍、周依然、于適主演的《我的阿勒泰》正在央視一套播出。
此前,第7屆戛納電視劇節(Canneseries)公布入圍名單,《我的阿勒泰》入圍最佳長劇集競賽單元,成爲首部入圍戛納電視劇節主競賽的長篇華語劇集。

這部只有8集的迷你劇首開先河上星央視一套黃金檔。
作品以輕喜劇的敘事風格向觀衆展示普通人找尋真我的心路曆程,是一個帶著輕盈詩意和散文韻味的電視劇。
截至2024年5月8日11時44分,該劇在愛奇藝的站內熱度破6000,連續多日登頂全網收視榜。

在口碑上,也是好評如潮。
曾經《去有風的地方》掀起了一股雲南旅遊熱,今年這部劇的播出,有人預測也許會帶來新一波的旅遊熱度。
不少網友說:“已經在查阿勒泰的攻略了”。

這部只有8集的迷你劇首開先河上星央視一套黃金檔。
作品通過質樸療愈的影像、輕喜劇的敘事風格向觀衆展示普通人找尋真我的心路曆程。
是一個帶著輕盈詩意和散文韻味的返鄉故事,也是一部美學獨樹一幟的影視作品。

《我的阿勒泰》根據作家李娟的同名作品改編,這是一本長銷十余年的自傳散文集。
作者以細膩樸實的筆觸還原了新疆阿勒泰地區生活的風貌。
現實生活中,李娟從小跟著母親來到新疆生活,她把在新疆阿勒泰的生活趣事和種種見聞,都寫進了《我的阿勒泰》裏。

新疆阿勒泰以哈薩克民族爲主,李娟一家是那裏是少有的漢族人。
李娟的媽媽在當地開了一間小賣部,李娟在縣城工作不順利,便回到阿勒泰與媽媽一起經營小賣部。

劇版《我的阿勒泰》講述了李文秀(周依然 飾演)這個漢族少女在追求文學夢想的道路上所經曆的挫折與成長。

劇集開篇,19歲的李文秀在烏魯木齊的餐館打工。
性格內向自卑的文秀始終懷揣著一個文學夢,卻因讀書不多而被嘲笑。
在搞砸了餐館一次重要的接待之後,李文秀不得不收拾行李,拿著被同事騙剩下的遣散費,不遠千裏回到阿勒泰投奔母親張鳳俠(馬伊琍 飾演)。

後來,李文秀又結識了哈薩克族少年巴太(于適 飾演)之後,她漸漸發現生活之美、生命之美。

近年來,返鄉劇已經成爲熒屏女性題材創作的新類型。
在這類故事中年輕的女主人公往往遭遇職業瓶頸返鄉,並在返回家鄉後遇到帥氣的男主角,由此在女主角尋找人生意義的主線劇之外輔以愛情支線。
《我的阿勒泰》使用了返鄉劇常見的故事模板。

作爲首部散文影視化改編的作品,《我的阿勒泰》成功的戲劇化改造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散文作品弱情節的問題。
這部劇的獨特之處在于地域特色,展現了阿勒泰的絕美風光和哈薩克族牧民的原生態生活。

劇中主角母女的劇情線也有不同以往的打開方式。
馬伊琍飾演的母親張鳳俠是從江蘇來的知青,丈夫早逝,一個人照顧癡呆的婆婆。
雖不是草原兒女,張鳳俠身上卻有一種反世俗常規、極具原始生命力的俠氣,她大膽灑脫用堅韌智慧解決生活難題。
馬伊琍在角色演繹上突破形象,诠釋這個異于常人的奇女子身在曠野的野性和粗粝,全無《繁花》中夜東京老板娘的精致感。

有觀衆表示,散文要進行影視化的改編並不容易,需要建立清晰的人物性格和故事走向。
同時又保留原著清新質樸、散淡美好的風格。
但目前來看感覺還不錯,影像質感在線,大自然的治愈和青年的野性十分令人著迷。

就像有人說的,如果新疆是離天堂最近的地方,那麽阿勒泰就是天堂的中心。
雖然劇集開篇時還不是阿勒泰最美的夏秋季節,但阿勒泰的冬季也令人印象深刻。
4K超高清拍攝下,阿勒泰的曠遠感被描繪得令人心曠神怡,又略帶幾分蒼茫孤寂。

天空呈現出冬日特有的高遠與清澈。
盡管冬已深沉,大地沉睡,四周的草木大多已褪去夏日的繁華,枯黃一片,仍有不屈的綠意頑強地穿透季節的嚴寒,點綴在蒼茫大地。
樹木尤其是那些耐寒的松柏,挺拔地矗立,在一片寂靜中顯得尤爲莊嚴,向世人訴說著關于時間、生存與堅持的故事。

對于散文改編有網友表示,影視化還原了不少文章裏的細節,很好地尋找到了一種平衡。
例如在李文秀一家三人去澡堂的這一段。
李娟曾經寫道:在澡堂洗澡,我這平凡的身子,平凡的四肢,不久後將裹以重重的衣裳,平凡的走在黃昏之中。這平凡的生活,這平凡的平安。我不再年輕,但遠未曾老去。
而劇中水氣氤氲,歌聲影影綽綽的澡堂,平靜而自然地呈現著作者的這種心境,氛圍與散文中的描述奇妙地契合在了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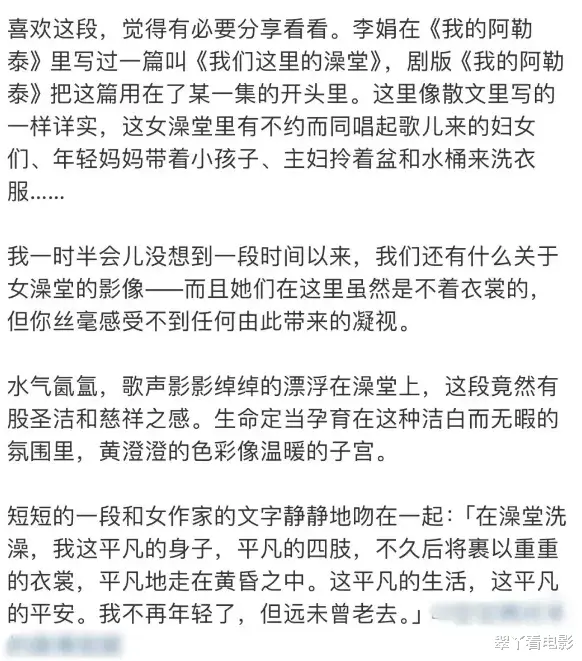
比較出乎大家預料的是,雖然整個片子看起來有一種滿滿的文藝感、
但又在某些時候走了一條輕喜劇的路線,同李娟筆下的文字一樣輕盈。
例如在李文秀被烏魯木齊的餐廳開除後被迫回到阿勒泰,大巴搖搖晃晃坐了一整天,母親電話打不通在戈壁灘裏迷路。
趕上放牧,她被樹上掉下來的面骨嚇得到處亂竄,終于回家睡覺了,床還塌了......

李文秀的生活屢屢笨拙碰壁,一切都不太順利。
但是奇妙的是,這些並不令觀衆感到壓抑,反而有一種“人在囧途”的喜劇效果。
有網友稱,阿勒泰像是徐徐清風,李文秀在笨手笨腳的生活,也在慢慢的實現自我治愈,生活的重量是輕盈的。

李文秀因爲母親張鳳俠飾在牧民的定居點開設小賣部,“闖入”其中。
在幫助母親討債的過程中,她很快發現這裏人與人相處的不同之處:
“這深山的社會看似遠離現代的文明秩序,實則有著自己的心靈約束。那種人與人相互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本能的相互需求所進行的制約是有限的,卻也是足夠的。”

在一個相對封閉且人際交往稀薄的環境中,由于缺乏外在強加的規則,人際關系的建立更多依賴個體間的相互理解和信任,直率且坦誠,促進社區內部的緊密聯系。
同時,心靈的自我約束和相互扶持構建了一種精神上的豐富。

在討債成功之後,她與母親這段“有用的人”的對話也引起不少共鳴。
李文秀十分開心,稱自己還是個有用的人,而母親張鳳俠卻問:“啥叫有用?”
“你看看這個草原上的樹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要是沒人用,它就這麽呆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自由自在的”,這段對話不少網友表示,心裏感動又敞亮了。



劇集捕捉阿勒泰自然景觀的壯麗與甯靜,也反映牧民生活與大自然的和諧共生。
以及他們在定居生活中對傳統與現代、自然與人文之間微妙平衡的探索與維護。
觀衆能感受到那份既遙遠又親近的曠遠之美,體驗到一種超越日常喧囂的心靈洗禮。

但坦率地說,如果《我的阿勒泰》只是簡單地拍成“宣傳片”,只是給觀衆帶來這樣一種感覺:
遠方太美、太治愈了,當下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遠方才是值得奔赴的,如此等等。
那麽劇集不僅是對散文豐富性的極大簡化,也會落入以往鄉愁文學的窠臼中——對遠方的單一幻想。

想象遠方的“美”,是如今越來越流行的一種“都市病”。
在快節奏、高壓力的都市生活中,很多人渴望逃離,尋求一片淨土。
劇中,李文秀也是在都市中處處碰壁後——寫作被嘲笑、打工不適應。
甚至連本以爲真誠的廣東仔高曉亮(蔣奇明 飾演)也坑了她一把,她才無奈回到阿勒泰投靠母親。

雖然李文秀對于“遠方”並無遐想,但她的經曆卻很“都市”。
從影視作品到各類短視頻中,我們經常看到關于“遠方”美的歌頌。
宣泄現代人對于當代生活的不滿,滿足他們對于簡單、純淨生活的向往和想象。
這樣的遠方想象非常單一。

遠方被構想爲沒有當前生存問題的烏托邦,實際上每個地方都有其獨特的挑戰和困境。
理想化的想象忽視了地域文化的多樣性和現實生活的多面性,構建一種不切實際的單一美好圖景。
同時,將遠方視爲解決個人問題或不滿的靈丹妙藥,反映出一種逃避現實的心態。
這種幻想暫時提供心理安慰,而非鼓勵面對並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問題。

劇集《我是阿勒泰》的導演滕叢叢會進一步放大這些情感。
將阿勒泰的自然美景、淳樸生活以及作者所感受到的甯靜與自由,進一步理想化地呈現給觀衆。
使阿勒泰成爲遠離都市喧囂、回歸自然生活方式的“遠方”象征。

《我的阿勒泰》是滕叢叢執導的第一部電視劇。
在此之前,爲了尋找適合用鏡頭呈現的阿勒泰故事,滕叢叢早已“跋涉”了許久。
這一次,她想講述的母題,關乎遊牧文化與現代文明,關乎代際沖突,更關乎每個人之間的尊重。

在原著中,“媽媽”是一個特別聰明的女人,她能一一記住來小賣店的人,也會在漢話和哈薩克語之間創造出無數新詞。
媽媽的聰明和堅韌在劇中有了更豐富的呈現。

同時,根據原作的一些人物的啓示,以及導演、編劇在采風中相識的友人,劇中創作出了男主角“巴太”(于適 飾演)的角色。

李文秀除了有自己的成長線,還有跟巴太的感情線,兩條線都貫穿始終。
而媽媽的角色堅強,樂觀,灑脫,代表了一種蓬勃的生命力。
文秀受到母親的影響,逐漸成長,最後跟母親相互扶持,這構成了整個故事的核心。

電視劇播出時,許多彈幕提到了導演和編劇都是女性,因此捕捉到了女性真正的美好與力量。
在原著中,祖孫三代女性在曠野中相依爲命的場景讓創作者們非常感動。
于是她們也希望從這三代人的身上,看到歲月和命運在不同年齡的女性身上留下的痕迹。

她們雖然有痛苦和迷茫,但總是能找到生命的支點,甚至在苦難中大笑出聲,在危險面前挺身而出。
她們就是那種你在難過的時候想要抱一抱的人。
她們也是那種剛幫你擦完眼淚,就開始跟你開玩笑,打趣你的人。

現在流行一句話:人生不是軌道,是曠野。
祖孫三代女性就生活在貨真價實的曠野之中,風吹雨打,叫天天不應。
但又怎麽樣呢?兵來將擋,水來土掩。
這就是曠野中的生存智慧,也是曠野賦予哈薩克人的生存智慧。

相較于“美”,阿勒泰的“遠方”中也有它巨大的疼痛。
這從阿勒泰典型的牧民家庭巴太(于適 飾)一家中鮮明體現出來。
巴太的哥哥長期酗酒,欠賬,對家庭不負責任。
對妻子托肯(阿麗瑪 飾)缺乏關懷,托肯提出離婚,丈夫卻不同意。

在一次醉酒從馬背摔下後,巴太的哥哥凍死在寒冬夜裏。
原本巴太是一名在伊犁的養馬人,他野性而自由,他喜歡馬,也有養馬的天賦。
哥哥去世後,他被父親要求回到牧場,“子承父業”。

還沒有離婚,丈夫就已經死去,托肯仍執意要改嫁,但巴太的父親不同意。
父親甚至要求巴太依照當地的習俗,與嫂子一起生活,共同撫養哥哥的兩個孩子。

巴太不同意,他跟嫂子說,他會勸說父親。
托肯無奈冷笑一下,“你說了算嗎?這不是爸爸說了算……男人想去哪兒就去哪兒,我們女人要做飯、洗衣服,還要看孩子,想出去一趟都沒有時間。我跟你哥說過很多次,去小賣部給我買搓衣板,直到死也沒帶回來。”

這片被譽爲世外桃源的土地並非全然無憂,它承載著生活的多重面貌,不乏現實的棱角與艱辛,暗湧著人性的掙紮與無奈。
妻子們被家務瑣事纏身,如同被無形的繩索捆綁在傳統的角色定位上,尋求解脫卻屢遭社會習俗的束縛,離婚之路荊棘滿布,自由如同遙不可及的夢想。

對于巴太這樣的年輕一代,理想與責任的沖突如同草原上兩股不可調和的風。
他們懷揣著對外界的憧憬與個人理想的火種,卻不得不在家族傳承與自我追求間做出抉擇。
巴太被傳統與父輩的期望緊緊捆綁。

通過這些細膩而真實的描繪,電視劇《我的阿勒泰》不僅展現阿勒泰生活的多維度。
也讓觀衆意識到,即便是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人間的疼痛與挑戰依舊無處不在。
我們覺得特別治愈的遠方其實美得直抒胸臆,卻也有凶猛且嚴苛的挑戰。

而馬伊琍飾演的張鳳俠這個角色,既是李娟筆下母親形象的映照,也背負著滕叢叢對新型母女關系的期待——互不幹涉。
這可能是阿勒泰的風光之外,劇中最“童話”的一個設定。

張鳳俠以阿勒泰爲舞台,向世人展示何爲真正的樂觀豁達,如何在逆境中找到灑脫與自在。
出場時,被幾名當地婦女圍坐在中間的張鳳俠,正在教她們說粗口。
轉過身,她又展現了自己的 " 創造 " 能力。
石頭壘成方框,再放幾只雞在後面,就成了正在播放中的 " 教你養雞 " 農業節目。

李文秀說想買倉鼠,她反駁說 " 你還嫌咱家耗子不夠多 "。
女兒看中了籠子裏的袖珍兔,她則表示 " 養一年都不夠炒一盤菜的 "。

可是,只要天不塌就耽誤不了睡覺,人前時刻都給人豪爽快樂感覺的張鳳俠,在夜色中回眸望過來時,身上原來也有沉重的底色。
她不是生來堅強,只是在人生的道路上,學會了前進的方式。

她的故事成爲一束光,照亮在不同文化和環境中的生存智慧,也是對所有追求幸福生活的人們的一次深刻啓發。
生活的美好不在于你處于何種地理位置,而在于你如何把握生活的方向盤,用樂觀、智慧、勇氣和愛,駕馭生活的波瀾,收獲屬于自己的幸福。

有網友評論說,《我的阿勒泰》不許拍愛情戲,拍了就俗了。但導演則覺得,如果認爲理智、冷酷、自私、只愛自己才是一種強大,那也是(有失)偏頗的。女性的多情、浪漫、包容、共情力、慈悲心……也是一種強大。

劇中有很多女性角色,處于我們非常熟悉的道德困境之下。
但劇集裏呈現出的三觀是,不論男女都不要在關系中過度地奉獻、犧牲。如果你得不到對方的認可和肯定,只會讓自我感動演變成怨恨。
彼此獨立不是自私。我們的世界是廣闊的,在追求經濟獨立的同時,首先要愛自己、認同自己。
這件“非常基礎的事情”,能幫助我們營造出更好的世界。

被選中的《我的阿勒泰》,回應的不只是女性的困境,對迷茫的年輕人而言,亦堪以告慰。
在當今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一部文藝作品若能突破重圍,贏得廣大觀衆的心,實屬不易。這樣既有 " 純氧 " 風的草原美景,又有生活味道濃郁的人物,敘事畫風既寫實又詩意的《我的阿勒泰》就像是一道清流。用最質樸而單純的方式,告訴我們應該怎樣 " 去愛,去生活 ",甚至是 " 去受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