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第五建利
邯鄲三惡少虐殺案,是一起挑戰和沖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霸淩慘案。它向我們提出了一個“法律到底在保護什麽人”的問題:在保護未成年受害人,還是在保護未成年加害人?這個問題的實質,不是別的,正是客觀存在的未成年人的逆保護。
什麽是未成年人的逆保護?就是說,在未成年人保護實踐中,客觀上受到實質性保護的不是未成年受害人,而是未成年加害人。其具體表現是:給予未成年加害人的是追西風、趕時髦的教條主義濫保護;給予未成年受害人的是非主流、打醬油的形式主義虛保護。
邯鄲三惡少以團夥式霸淩,長期針對一個弱小善良的同班同學,最終凶殘殺害之。他們蓄意謀殺、共同作案,劫財害命、毀容埋屍,悍然行凶、淡定應對。暴戾而貪酷,冷血而狡詐。視人命如草芥,視國法如空文。主觀惡性極大,手段特別殘忍,過程血腥恐怖,情節極端惡劣。不嚴懲不足以平民憤,不嚴懲不足以安民心,不嚴懲不足以顯公平,不嚴懲不足以伸正義,不嚴懲不足以保平安,不嚴懲不足以護穩定。

他們雖然已被核准追訴,但不等于逆保護不存在了。《未成年人保護法》第三條規定,國家保障未成年人的生存權、發展權、受保護權、參與權等權利。第四條規定,保護未成年人,應當堅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則。處理涉及未成年人事項,應當符合“給予未成年人特殊、優先保護”等六項要求。具體到邯鄲三惡少虐殺案,受害人和加害人都是十三周歲,而受害人的生存權、發展權、參與權均已被加害人凶殘地剝奪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還要給予加害人特殊、優先保護,每人先賞一顆“未成年人不適用死刑”的定心丸,再送一個“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的大禮包,這等于受害人連僅剩的受保護權也嚴重縮水了。最後,把加害人在未成年人管教所裏充滿關愛地養起來。對比之下,傷害何其大也!這公平嗎?這正義嗎?向來如此就對嗎?保護未成年人,應當最有利于未成年受害人,還是最有利于未成年加害人?以善報惡,何以報善?
“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是千百年來老百姓的樸素公平正義觀的最大公約數。當年劉邦破秦入關,與關中父老約法三章,第一條便是“殺人者死”!如果我們的法律既治不了霸淩殺人的惡少,又治不了欠債不還的老賴,那麽,老百姓有什麽理由相信法律?法律的權威又從何而來?電影《第二十條》有句台詞說得特別好:“法律的權威來自哪裏?來自老百姓最樸素的情感期待。”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法律,毫無疑義應當堅持人民性與權威性的有機統一。法不能向不法讓步,法不能對惡少縮水,法不能遇難題躺平,法不能跟老百姓的樸素公平正義觀對立。說老百姓是法盲很簡單、很容易,但法律要贏得老百姓的信任不簡單、不容易。正如演出效果不佳不能怪觀衆不懂戲一樣,法律效果不佳不能怪群衆不懂法。究竟是老百姓不懂法律,還是法律不懂老百姓?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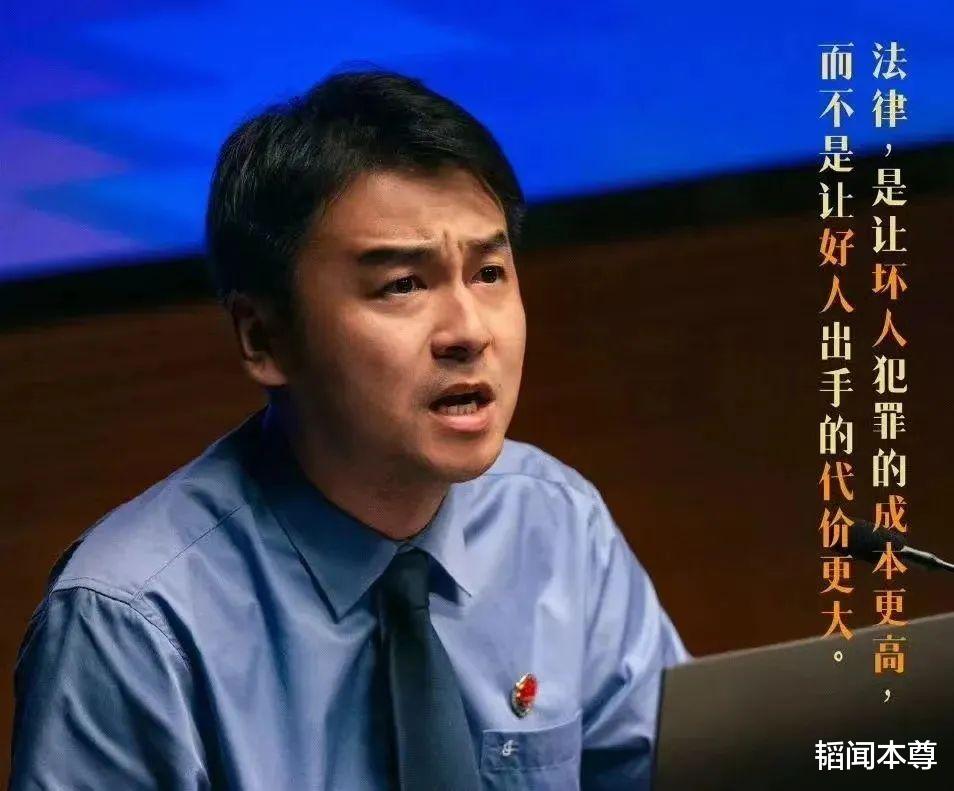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判斷法治是不是良法善治的根本標准,就是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什麽叫人民至上?這就叫人民至上。什麽叫以人民爲中心?這就叫以人民爲中心。老子講得透徹:“聖人常無心,以百姓心爲心。”民間常說,“別把羅成當娃娃”。邯鄲三惡少的作案過程和事後應對表現充分證明,他們是典型的羅成式犯罪嫌疑人,是事實上的低齡型超成人,是國人皆曰可殺的校園小惡魔。我們憑什麽要像唐僧對白骨精那樣對三惡少發慈悲心、當爛好人?如此喪盡天良、滅絕人性的未成年三害,理應是我們嚴厲、沉重打擊的對象,決不是我們特殊、優先保護的對象。
曆史唯物主義認爲,群衆是真正的英雄和智者。人民群衆對邯鄲三惡少是什麽態度呢?是必欲判其死刑而後快!從來沒有哪起案件像這起案件這樣持久地牽動著全國上下、社會各界、千家萬戶的視線和神經。人民的憤怒在輿論場上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某些“法學東郭先生”,習慣性地把所謂“情緒化”的標簽硬往群衆臉上貼,卻絲毫看不到隱藏在其法律書袋裏的無窮後患。他們的說教無異于“虎狼屯于階陛尚談因果”,豈不聞“下下人有上上智”!邯鄲三惡少窮凶極惡、慘無人道地剝奪了一個毫無過錯的同齡人的生命,人民群衆要求依法“剝奪剝奪者”天公地道。因爲我們是爲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的法治也是爲人民服務的。只要我們爲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爲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我們的法治就一定會不斷進步。相反,如果我們不尊重人民意願,不嚴懲邯鄲三惡少,那麽,我們的法治就會失去人民的信任,極有可能導致叢林法則盛行、以暴制暴成風的災難性後果。能動司法之人民立場的真谛是什麽?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將心比心,正義自見。對被害孩子的家長來說,法庭判決應當是伸張正義的鐵拳,而不是自嗨理性的雞肋。
現實版“紅孩兒”們憑什麽敢肆無忌憚地興妖作怪?他們憑的是法律“三昧真火”:一是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這個公約把十八歲以下的任何人統稱兒童,明確規定不得對犯罪兒童判處死刑或無釋放可能的無期徒刑。中國是締約國之一。二是《刑法》第四十九條。這個法條規定,犯罪的時候不滿十八周歲的人不適用死刑。三是《未成年人保護法》。該法第一百一十三條規定,對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堅持教育爲主、懲罰爲輔的原則。嚴重的問題在于:上述法律善意正在被未成年作惡者惡意利用,變成了他們對付執法者、司法者的護身法寶、反攻利器。
恩格斯指出,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我們應當怎麽辦?我們應當解放思想,開動腦筋,拿起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武器,破除對法律的迷信和執念,聚焦霸淩案,扭轉逆保護,把顛倒的是非重新顛倒過來。
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是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在當今互聯網時代的社會生活中,未成年人的具體情況是怎樣的呢?未成年人身體心智早熟化、違法犯罪低齡化、犯罪方式團夥化、犯罪手段成人化、重新犯罪突出化、惡性犯罪殘忍化、作惡成本超低化,而他們利用法律善意的能力和反偵查能力卻在野蠻生長。他們不守法並不是因爲不知法,而是因爲不畏法。他們要鑽的就是法律的空子,像吃青春飯那樣犯少年法,倚小賣小,氣焰囂張。在一些未成年加害人那裏,教育和法治非但不是萬能的,簡直就是無能的:教師不敢管、管不了,學校不敢開、開不了,警察不敢抓、抓不了,法官不敢判、判不了。師道尊嚴和法律權威在他們的心目中壓根兒就不存在。這些被法律供起來的未成年加害人,反倒變成了“聖嬰大王”式的國民小祖宗,真是豈有此理!對這種令人憤懑的法律善意反效果,警察和法官既窩火、又憋屈,但卻無能爲力;早已失去戒尺的教師除了和風細雨外,只能是日益佛系;善良的人們心甚憂、意難平,正所謂“我本將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再沒有比這更大的“天下之憂”了,凡此種種,人民群衆強烈不滿久矣!

生活、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觀點。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判定法律之是否良法,同樣依此而定。生活經驗和實踐真知告訴我們,成年人欺負未成年人的案件確實有,但不多;大量的類似案件是發生在未成年人之間的霸淩案件。而在未成年人惡性犯罪案件中,受害人絕大多數是弱小無助、勢單力薄的那一部分未成年人。最常見的霸淩是“多打一”模式,雙方的力量對比,是加害方對受害方的碾壓式絕對優勢。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客觀事實。在這類案件中,區別對待未成年受害人和未成年加害人顯得尤爲重要。否則,所謂未成年人保護只能在客觀上起到保惡屈善、護強抑弱、厚衆薄寡、鼓勵人性之惡的反作用。
正如沒有區別就沒有政策一樣,沒有受害人和加害人的區別就沒有未成年人保護的公平正義。譬如在一起強奸殺人案件中,加害人不滿十二周歲,被害女童年僅四歲,結果是加害人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真可謂逆保護的冰火兩重天!法律對這個女童的保護承諾,竟然是口惠而實不至,保了個落花流水春去也。法律對她這個未成年至弱者何其不利、何其不公、何其無情!于是乎,我們的法律陷入了自身的尴尬悖論:保護了惡意滿滿的作孽強者,辜負了長恨綿綿的可憐弱者。
事物的矛盾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的法則。自然、社會和思維無不遵循矛盾法則。差異就是矛盾。爲什麽會出現未成年人的逆保護?因爲未成年人保護嚴重忽視了矛盾的特殊性。其結果是:給予未成年加害人的保護,是具體的、實質性的、全方位的、一條龍一整套的;給予未成年受害人的保護,是抽象的、表面性的、空泛化的、無後續無措施的。我們往往不自覺地讓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代表”所有未成年人來享受法律保護、享受合法權益保障,用自以爲是的法治進步換來了事與願違的情理倒退。全面保護未成年人,這是矛盾的普遍性;在區別未成年受害人和未成年加害人的基礎上實行差異化保護,這是矛盾的特殊性。只有堅持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辯證統一,才能掌握未成年人保護的規律。對反複出現的問題、普遍存在的問題,應當到全局指導上找原因。我們的未成年人保護,必須堅持全面貫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原則。我們的未成年人保護,必須堅持最有利于未成年受害人的原則。我們的未成年人保護,必須堅持同一案件未成年受害人權益保障優先、未成年加害人權益保障限制的原則。我們的未成年人保護,必須堅持依法追究加害方監護人責任的原則。

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並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當前,人民群衆反映最強烈的法治領域的突出問題是什麽呢?就是大家普遍認爲:法律對壞人太好,對惡少太善。真正的法治必然拒絕聖母心,因爲聖母心泛濫的結果就是“法治聖母”被“聖嬰大王”先奸後殺,到死還在念叨:“抛開事實不談,他還是個孩子,不適用死刑……”這叫什麽?這叫主觀和客觀相分裂、認識和實踐相脫離。
馬克思主義者是立法本意與法律效果的統一論者。邯鄲三惡少把一道法治難題挑釁性地扔在了我們面前,人民群衆高度關注,考驗各方神聖的智慧和勇氣的時候到了!我們的專家學者怎麽看?我們的代表委員怎麽說?納稅人的錢總不能白白花在刀鞘和刀背上而與刀刃毫不沾邊吧?俗話說,活人不能讓尿憋死。針對現實版“紅孩兒”們的法律“三昧真火”,竊以爲可以用如下四個辦法來滅火伏魔、扭轉乾坤。
第一,正名劃線,一分爲二。孔子論爲政之先務說:“必也正名乎!”按照我們的民族習慣,我們可以對未成年人實行一分爲二的正名劃線:十二周歲以上、不滿十八周歲屬于少年;十二周歲以下屬于兒童。這樣,對三惡少判處死刑,就並不違反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中國有句老話,男子十二奪父志。我們的古人甘羅十二歲就憑真本事拜相當領導了。我們認爲,把未成年人一律視爲兒童是荒唐可笑的,是嚴重缺乏人類發展自信的。事實上,我們的中學生從來不過兒童節。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好比是統一戰線,我們區分少年和兒童好比是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我們要嚴懲的邯鄲三惡少不是兒童,而是少年,因此不受這個公約的約束。什麽叫中國特色?這就叫中國特色。什麽叫走自己的路?這就叫走自己的路。
第二,拿來主義,洋爲中用。大膽引入英美法系的“惡意補足年齡”規則,爲我所用。一則邯鄲三惡少的犯罪惡意遠遠超過成人,應當按照成人標准定罪量刑。二則受害人和三惡少同爲十三周歲未成年人,理應按照未成年抵消規則對三惡少實行權益保障限制,適用成人量刑標准。同時,建議發揚司法首創精神,組建人民陪審團參與此案審判,把能動司法建設推向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第三,原心議罪,古爲今用。法治文明不是西方國家的專利。我們的古人有著非常務實而高明的司法智慧,例如“原心定罪”原則和“嚴誅首惡”原則。馬克思主義法學就是曆史唯物主義法學,從《唐律疏議》到《大清律例》,我們都要以“兩個結合”的精神批判性地吸收其法治精華。清代乾隆年間,一個九歲男孩霸淩另一個九歲男孩,強吃惡要零食,致後者倒地斃命,被判處絞監候,相當于我們現在的死緩。乾隆皇帝表示,如此惡童,決不減刑。邯鄲三惡少比這個惡童年齡大得多、惡意深得多、罪孽重得多,難道他們不該被處以極刑嗎?
第四,修改法條,創設規則。自覺的能動性是人類的特點,我們可以在充分討論、集思廣益的基礎上修改有關法條,並科學創設新的法治規則。比如說,我們可以在規定刑事責任年齡的同時,特別規定受害人是未成年人的惡性犯罪案件,追究刑事責任不受年齡限制。比如說,我們可以考慮再次下調刑事責任年齡。下調的本身,就是對未成年人惡性犯罪的超前震懾和積極預防。比如說,既然有特赦令,爲什麽就不能有特懲令?打破思維定勢,一切皆有可能。
辦法總比困難多,關鍵在于我們有沒有大無畏的反潮流精神,敢不敢做第一個吃螃蟹的法治孤勇者和規則創立者。沒有先例,那就創造先例。上述辦法可以概括爲一句話:未成年人虐殺未成年人者死!

法律,歸根結底是治國理政的工具。法律之劍,貴在鋒利,不貴時尚虛名,正所謂“良劍期乎斷,不期乎镆铘”。法律,也要講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群衆的呼聲,就是我們立法修法的努力方向。我們的法律,決不能聽滿世界賣人權拐的僞善海盜的忽悠。我們曆盡艱辛追尋良法善治,蓦然回首發現:實事求是和群衆路線,才是我們做好包括立法修法工作在內的一切工作的根本保證。
法治是沒有標准答案的,最管用的就是最好的。世界上不存在一旦制定、萬古不變的法律教條,更不存在四平八穩、雷打不動的法治進步。我們認爲,死刑的震懾作用無可替代,判處死刑是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該判死刑而不判死刑,才是脫離群衆,不得人心。邯鄲三惡少是一個霸淩殺人犯罪團夥,理應均以主犯論處,不存在什麽從犯,而只存在主犯中的首犯。爲了保護最大多數未成年人的安全,極刑嚴懲未成年三害,就是最大的人道主義,也是最大的尊重和保障人權。這叫什麽?這叫以霹雳手段,顯菩薩心腸。
塑造什麽樣的“中國少年”,就會有什麽樣的“少年中國”。這些年來,我們保護未成年人的最大失誤,就是把未成年加害人慣成了法律的寵兒、社會的熊孩,未成年人保護異化爲單純優待劣迹少年。二十年前,某市綁架殺人的四名未成年罪犯躲過死刑、相視而笑的場景實在氣人。他們作案前早就知道自己是“判不死的小強”,所以才決定“犯罪要趁早”。二十年後,霸淩虐殺同學的邯鄲三惡少,年齡更小,罪行更惡。二十年來辨是非,善花開處惡果結。血的教訓啓示我們:未成年人保護工作,必須堅持兩手抓、兩手硬,一手抓全面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權益,一手抓嚴厲打擊未成年人惡性犯罪。就是說,爲了教育挽救大多數,必須嚴懲重處極少數。只有這樣,才是符合對立統一法則的未成年人保護,才是符合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的未成年人保護。
王陽明說:“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立法修法和執法司法的過程,就是我們致良知的過程。如果我們抱著宋襄之仁、尾生之信,死守“未成年人不適用死刑”的教條不變,甯可負天下人,也不負三惡少,那麽,悲劇的重演就不可避免。
年齡有大小,人性無大小,欺軟怕硬、恃強淩弱的人性之惡,才是三惡少犯罪的實質性主導。留守是外因,善惡是內因,自私冷酷、漠視生命的內在之惡,才是三惡少犯罪的決定性因素。對這等貨色選擇節約公共資源,堅決送其往生才是大仁大義的上策。若容許罪大惡極者留得青山在,好人遲早會遭火燒。請大家用逆向思維來認真想一想,假如邯鄲此案久偵未破,甚至受害人糊裏糊塗“被失蹤”了,三惡少會不會良心發現,投案自首?會不會幡然悔悟,金盆洗手?絕對不會!他們只會更奸更惡更老練,而遭其禍害的孩子也只會更多更慘更可憐。作爲學生家長、作爲孩子父母,就說你怕不怕?敢不敢往下想?誰能保證今後不會再發生類似案件?須知:最狠的打擊才是最好的預防。

當前未成年人保護的主要矛盾是什麽?其主要矛盾是:未成年受害人的權益保障需求與未成年人保護不全面、無區別甚至更偏重對未成年加害人的權益保障之間的矛盾。感覺只解決現象問題,理論才解決本質問題。量變已經足夠,質變就在眼前。我們應當以最大的曆史自覺,來推動未成年人保護的質變的發生。嚴懲邯鄲三惡少,就是實現這個質變的破局第一刀。我們的法治,要以取經趕考的精神務實擔當,傳承紅色基因;這個紅色基因就是: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堅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努力讓人民群衆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我們的法治,要以察今變法的精神砥砺奮進,彰顯文化自信;這個文化自信就是: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捍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我們主張嚴懲邯鄲三惡少,不僅是要嚴厲打擊未成年人惡性犯罪,而且是要堅決捍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三惡少對同窗學友非但不誠信、不友善,反而包藏禍心、惡毒至極,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尖銳對立,于情于理于法,皆是背道而馳,此風決不可長。爲什麽古人對逆倫案的罪犯要殺無赦甚至還要罷縣令的官?就是爲了捍衛當時“聖朝以孝治天下”的核心價值觀。自古邪不壓正、法不容惡,古人的治理智慧值得我們虛心借鑒:對邯鄲三惡少,一個都不寬恕!
有一種創造叫打破,有一種擔當叫轉折。社會各界都在等。等什麽呢?等邯鄲三惡少的最終結局。不但我們成年人在等,未成年人也在等,潛在的霸淩者更在等。我們堅信,嚴懲邯鄲三惡少,必將成爲中國法治史上具有裏程碑意義的標志性事件。它是廣大未成年人拒絕校園霸淩的良好契機,它是全社會爲未成年受害人施以援手的公益維權,它是以法治方式捍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播種機,它是用法治思維開辟未成年人保護新境界的宣言書。

可憐天下父母心,誰忍子女遭霸淩?盼望自己的子女健康成長、平安成長、快樂成長,是人民對美好生活的第一向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三害不除,霸淩未已。這是一個關乎最大多數人的利益的問題,我們沒有理由沉默。讓我們代表人民的利益和願望大聲疾呼:嚴懲三惡少,扭轉逆保護,還未成年受害人以公道,給所有未成年人以教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