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網絡輿論上突然有大量營銷號不約而同在刷同一份通稿,內容大同小異,都在說“4月23日,堪稱中國貨幣史上重要的一天”,甚至謠傳“4月23日開始,央行將把在二級市場上買賣國債常態化”,動辄說我們央行也要開始搞量化寬松。

他們都提到4月23日,還貼了人民日報在4月23日的一篇文章。
秉持求證精神,我就具體去看了下這篇《堅持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但這篇文章原文是說“支持在央行公開市場操作中逐步增加國債買賣”。
這並沒有什麽問題。
結果,到了那些營銷號嘴裏就成了“買賣國債常態化”,變成我們也要搞量化寬松。
然而,量化寬松是指一個國家央行在實行0利率後,常規貨幣政策已經用盡,爲了刺激經濟,只能每個月印鈔購入固定金額的國債。
量化寬松的關鍵點是“量化”,具有長期、定額、定量的特點。
從“逐步增加國債買賣”,到“量化寬松”,是有很長的一段距離,二者並不能簡單等同。
這相當于我們只是提了個數字1,他們馬上誇大成1萬,就大肆渲染。
這已經屬于公開造謠。
而且,同樣在4月23日,央行都公開發聲表示,買賣國債與量化寬松操作截然不同。
已經做了一個辟謠。

央行這個回應全文是挺有意思的,我們可以具體來看一下。
央行是在對“長期國債收益率持續下行”這件事情,做回應的時候,專門提到“未來央行開展國債操作也會是雙向的”。

這裏就需要了解一個大背景。
過去兩年,我們10年期國債收益率處于持續下行狀態,從2.9%的收益率,一路下降到現在2.3%左右。

債券收益率和價格是反向關系。
我們國債收益率下降,說明國債價格上升,這意味著有大量資金在買入我們國債。
此外,今年一季度政府債券發行節奏整體偏慢,發行量同比少近2400億元。
于是,4月份以來,儲蓄國債出現“搶購”情形。
財政部方面在22日表示,“一債難求”核心就是需求旺盛,供給相對不足,所以下一步要研究適當增加發行規模等。
供給減少,但需求旺盛,才導致當前國債供不應求,才導致國債收益率持續下行。
國債收益率持續下行,也說明市場上的流動性比較寬裕,如果國債收益率持續上行,則說明市場流動性比較緊縮,連買國債的資金都變少了。
相比之下,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從2020年0.5%的曆史低點,一路上升到現在4.6%

這主要原因就是美聯儲激進加息,會帶動國債收益率持續上行,從而造成市場流動性緊縮。
在當前美債收益率居高不下的情況下,我們國債收益率持續下行,雖然代表我們國債吃香,但也會有一些負面影響。
比如會導致我們和美國的利差擴大,從而增加彙率貶值壓力。
此外,央行在4月23日的回應裏也說得很明確,長債對對利率波動比較敏感,投資者需要高度重視利率風險。
其中提到“對于銀行、保險等配置型投資者,如果將大量資金鎖定在收益率過低的長久期債券資産上,若遇到負債端成本顯著上升,會面臨收不抵支的被動局面。”
還舉了硅谷銀行這個典型例子。
硅谷銀行就是因爲在2020年美聯儲無限印鈔時期,買入大量低利率的美債,這意味著當時美債價格處于曆史高位,相當于追高買入。
結果美聯儲激進加息後,美債收益率飙升,價格暴跌。硅谷銀行購買的低利率美債就出現嚴重浮虧。
而硅谷銀行最大問題是“短債長投、期限錯配”,把大量存款和短期借款,拿去購買長期美債。
結果在出現嚴重浮虧後,投資者紛紛擠兌取款,硅谷銀行被迫抛售美債,浮虧就變成實虧,最終破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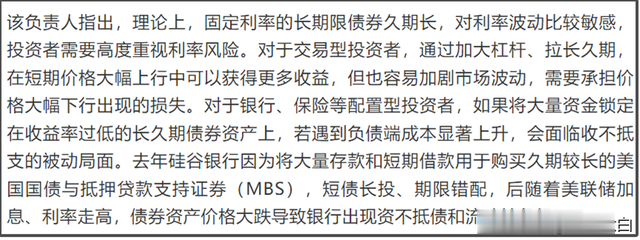
所以,央行這段話的意思是,不能讓國債收益率長期下行,否則銀行和保險如果配置太多的低利率國債,一旦未來利率走高,銀行和保險就會面臨較大風險。
國債收益率跟彙率一樣,過高跟過低都不好,長期保持在一個穩定的區間裏震蕩,才比較好,這就需要央行去適當調控。

我們10年期國債收益率,當前是處于曆史低位,如果我們這時候要穩定國債收益率,反而應該是賣債,而不是買債。
所以,央行在4月23日的回應裏才會說,“未來央行開展國債操作也會是雙向的”。
意思是,央行不但會買債,而且會賣債。
結果卻被很多人解讀爲“中國版量化寬松”,簡直南轅北轍。
其實,4月23日的這兩篇文章。
《堅持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財政方面寫的。
對長期國債收益率走勢的回應,則是央行方面回應的。
這其實代表財政和央行的兩個態度,二者是有微妙的區別。
這讓我想起,2020年也一度爆發的我們輿論上關于是否財政赤字貨幣化的討論,其實比現在要激烈得多。
財政赤字貨幣化,就是債務貨幣化,就是要央行去量化寬松。
當時是財政系學者支持赤字貨幣化,而央行系學者反對赤字貨幣化。
那一次大討論是央行系勝出,我們後來沒有搞赤字貨幣化。
而這次,估計圍繞著是否債務貨幣化的討論是卷土重來。
我個人觀點,一直是堅決反對債務貨幣化,不贊同搞量化寬松,支持適度買賣國債來進行貨幣調控。
這裏強調幾點,
1、量化寬松,不等于債務貨幣化,二者有程度區別。像日本這樣的超級量化寬松,才等于債務貨幣化。
2、一旦實施量化寬松,很容易踏上債務貨幣化的不歸路。
凡事有利有弊,量化寬松也不可能100%都是壞處。
如果有國家能有節制的去搞量化寬松,也是有好處。
但只要施行量化寬松,想要節制會非常難,目前沒有一個搞量化寬松的國家,是有節制的。
量化寬松很容易滋生“懶政”,一旦開啓量化寬松,很容易遇事不決就發債,會變成無節制發債。
所以,量化寬松就是甜蜜的毒藥,短期是很爽,但長期會很慘。
過去十幾年,搞量化寬松的國家也不少了。
發展中國家搞量化寬松的,現在通脹沒兩位數都不好意思見人。
就算歐美日等發達國家搞量化寬松的,現在也並不好過,後遺症已經十分明顯。
特別是日本這個踐行MMT貨幣理論,搞債務貨幣化的國家,現在已經面臨彙率長期貶值的局面。
日元彙率,最近已經貶值到1美元兌換155日元,相比2021年已經貶值了34%;

而美國也經曆了2022年的高通脹,直到現在仍然是通脹高企,面臨嚴重的債務負擔。
有這些國家的前車之鑒,我們怎麽能認爲量化寬松是一劑良藥沒有副作用呢?
目前來看,我們央行對于量化寬松的副作用,還是十分清醒的。
但也可以看出,我們央行也是頂著壓力,才能不搞量化寬松。
畢竟現在,我們內部房地産帶來的債務壓力,還有地方債壓力,還是比較大的。
所以,我們過去這一年,重點其實在“化債”。
但是,“化債”,並不意味著就得馬上搞量化寬松。
量化寬松是貨幣政策用盡後,不得已而爲之的最終辦法。
通常得把利率先降至爲0,才會開始搞量化寬松。
我們現在利率都還沒有降至爲0,很多人就開始鼓吹量化寬松,這是有問題的。
央行在23日的回應裏,說得比較明確,“一些發達經濟體央行在常規貨幣政策工具用盡情況下,被迫大規模單向買入國債來實現貨幣政策目標,而我國堅持實施正常的貨幣政策,人民銀行買賣國債與這些央行的量化寬松(QE)操作是截然不同的。”
還提到“央行在二級市場開展國債買賣,可以作爲一種流動性管理方式和貨幣政策工具儲備。”
把國債買賣作爲流動性管理和貨幣政策工具,跟量化寬松是有很大區別。
量化寬松的收益率曲線控制,通常會設在0利率附近,也就是把短債收益率控制在0利率。
但我們當前並沒有這樣的收益率曲線控制目標。
我們未來可能的做法是,如果央行覺得當前國債收益率持續下行會出問題,可能會抛售國債,來讓債券市場降溫,提高國債收益率。
如果國債收益率持續上行也出問題,央行可能也會買入國債,來降低國債收益率。
來把國債收益率調控在一個比較寬幅的震蕩區間裏。
這跟歐美量化寬松有很大區別,首先一個是單次買賣量不會太大,其次並不是一個長期、定期、定量單向買入的行爲,而是雙向的。
另外,《中國人民銀行法》第二十九條明確規定,中國人民銀行不得對政府財政透支,不得直接認購、包銷國債和其他政府債券。
同時第二十三條裏也明確規定,中國人民銀行爲執行貨幣政策,可以運用貨幣政策工具包括,在公開市場上買賣國債、其他政府債券和金融債券及外彙。
這個意思是,央行不能在一級市場直接認購國債,但可以在二級市場公開買賣國債。
絕大多數國家的法律也都支持央行在二級市場公開買賣國債,但這與施行量化寬松,是兩碼事。
我們雖然很少在二級市場直接買賣國債,但也有過曆史先例。
我們在2007年就購買過國債,當時爲了提高外彙資産運營收益,發行了特別國債。
2017、2022年央行購買國債,均是2007年特別國債部分到期後的續發國債。
當前央行持有約1.52萬億元國債,其中1.35萬億元就是2007年買的。
除此之外,過去這些年,央行往往是通過逆回購和MLF等貨幣工具放水給市場,來熨平發債時帶來的資金面波動。
這是我們2015年開始,主要的貨幣發行方式,就是把錢借給銀行等金融機構。

從央行資産負債表可以看出,2015年開始,外彙占款等國外資産占比是越來越低。
而央行對其他存款性公司債權的比例是越來越高,這是我們過去這些年的擴表主要方式。
而金融機構從央行那邊借到錢,通常就是拿去買國債或者變成房貸,因爲個人房貸在商業銀行的占比很高。
所以實際上,2015年開始,我們的貨幣發行,就從錨定美元,逐步切換到錨定我們自身國債和房地産。
這跟美國當前是一樣的,當前美國貨幣也是錨定在自身國債和房地産MBS債券。
美聯儲資産負債表65%是買了國債,30%買了房地産MBS債券。
而我們資産負債表裏,外彙占比48.5%,對其他存款性公司債權占比40%,也就是我們當前貨幣發行,已經有40%是錨定在自身國債和房地産。

綜上所述,我們換錨是2015年就開始了,不是那些營銷號所說的現在才開始。
而且換錨這件事情,跟量化寬松完全是兩碼事。
量化寬松並不是換錨的前提條件。
2015年之前,我們貨幣發行主要就是錨定在美元身上,是靠外彙儲備增加,來對內發行貨幣。
這顯然會讓我們缺乏對自身貨幣調控的主動性。
所以2015年之後,我們逐步貨幣換錨到自身國債和房地産,這是好事。
但我注意到,這次營銷號通稿裏,還有典型的把夾帶的私貨,寫成爽文的形式。
比如都不約合同寫著“央行將把在二級市場上買賣國債常態化。人民幣全球化是必然,是曆史的選擇,也是曆史的必然。”

這種爽文雖然普通人看著很爽,但實際是包裹著債務貨幣化的毒藥。
而且,人民幣全球化跟“量化寬松”沒啥關系。
量化寬松,並不是人民幣全球化的先決條件。
但在這些通稿裏,包裹著一個禍心,就是刻意營造這種氛圍,就是我們得先搞量化寬松,才能人民幣全球化,這是一種謬論。
人民幣全球化確實是曆史的必然,但不代表我們就一定得去搞量化寬松,才能人民幣全球化,這是兩碼事。
我們當前人民幣全球化,主要是錨定在我們龐大的制造業産能,基于龐大的貿易規模,再通過雙邊貨幣互換工具,把人民幣輸送到海外。
這些營銷號刻意把量化寬松跟人民幣全球化進行綁定,一方面是爲了寫爽文,來降低夾帶私貨的風險。另外一方面也是在裹挾輿論去給量化寬松造勢。
對此我們要有清醒認知。
最後,我還是要強調一下。
這只是我基于個人觀點,去反對量化寬松,跟我們最終搞不搞量化寬松,是兩碼事。
畢竟搞量化寬松的短期誘惑太大,未來某個時刻,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搞量化寬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比如,2008年次貸危機裏的美國,如果當時美國不施行量化寬松,去大規模印鈔購債,美國金融霸權可能就會瓦解,美國相當于直接被判了死刑。
而施行量化寬松,則至少幫助美國暫時把危機延後了十幾年,相當于是死緩。
這種情況下,從國家層面來說,大多數國家都會選擇在面臨危機時,去施行量化寬松,能拖一時是一時。
但這跟當前短期內,我們馬上就要搞量化寬松,也完全是兩碼事。
我個人觀點是,我們短期內搞量化寬松的可能性極低,因爲我們利率都還沒有降至爲0。
未來等到我們利率降至爲0,貨幣工具出盡的時候,才有可能被迫搞量化寬松。
但至少現在還沒有到那個時候。
而且,“支持在央行公開市場操作中逐步增加國債買賣”,這句話是去年就提出的,結果上個月輿論突然炒作量化寬松,我認爲是有點在配合做空彙率的意思。
我之所以反對搞赤字貨幣化,因爲這是甜蜜的毒藥,雖然可以把危機延後十幾年,但只會把泡沫吹得更大,會讓未來爆發危機時的破壞性更強。
而且,量化寬松會導致貧富差距更加嚴重,美國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
量化寬松所帶來的無限印鈔,首先會讓離錢近的人發財,會推升資産價格泡沫。
而不管房地産、股市、債市,都是富人配置最多的財産。
2008年次貸危機後,美國最窮的50%人群,和40%中産階級,過去十幾年基本原地踏步,只有最富有的10%人群,財富劇增。

所以,我們國內一直以來,也都是金融資本最喜歡鼓吹搞量化寬松,稍有點苗頭,就操縱輿論去大肆渲染我們要搞量化寬松的氛圍,因爲這些金融資本是量化寬松的最大受益者。
但我們普通人,在跟風鼓吹量化寬松的時候,得好好想想,量化寬松真的對我們有利嗎?
至少,在這場圍繞著是否債務貨幣化的大討論裏,我們作爲普通人最好還是要旗幟鮮明的站在反對債務貨幣化的立場。

正如央行過去幾年經常說的一句話“珍惜正常貨幣政策空間”。
本文來源“大白話時事”公衆號。
作者:星話大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