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彧是魏臣還是漢臣?曆來有兩種看法。時至今日,史家的看法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基本上沒有人認爲荀彧是魏臣,在論及他與曹魏的關系時,說他是曹操統一北方的功臣,是維護漢朝天下的忠臣。王永平說:“荀彧全力輔佐曹操,可謂盡忠盡責。但隨著北方的漸歸統一,曹操開始圖謀甩掉漢獻帝這個包袱,經營自己的天下。這對荀彧來說是極其殘酷的,意味著他寄希望于曹操恢複東漢王朝之舊貌的願望徹底破滅。”孟祥才說:“荀彧給自己設定的人生定位是:矢志忠于漢皇朝,盡自己的最大努力延續東漢國祚,甯做忠臣而慘死,不做叛臣以苟活。”
他仍然給曹操預設了一個人生定位:做權臣而不做篡臣。即曹操可以權傾朝野,挾天子以令諸侯,甚至可以擅自廢立,擁有皇帝擁有的一切權力,但是,曹操必須維護漢朝的皇統,將自己終生定在臣子的位置上。只要曹操不越過臣子的界限,就無條件地擁護曹操,爲曹操肝膽塗地而心甘情願。不過,如果曹操越過了這條界限,便與曹操分道揚镳,即便爲此而付出生命的代價也在所不惜。這些論述無疑反映了當代學者的看法,超脫了古人“魏臣還是漢臣”的窠臼。然而這些論述把荀彧分爲兩截:爲曹操服務忠心耿耿,發現曹操野心後分道揚镳。其實並非如此,荀彧始終是在維護漢朝的皇統,他和曹操在合作的表象下一直在暗中較量。
荀彧對曹操的幫助曹操是個有智慧的人,其智慧在政治、軍事、思想、文學等方面體現得淋漓盡致。荀彧是曹操的謀士,“發言授策,無施不效”,也是個有智慧的人。
初平二年(191年),當荀彧投奔曹操,曹操大悅,說荀彧是“吾之子房也”。曹操說荀彧是他的張良,這從荀彧對曹操的幫助亦見此言不虛。
興平元年(194年),曹操征陶謙,張邈、陳宮以兖州反,潛迎呂布,兖州諸城多被呂布所占,唯鄄城、範、東阿不動。荀彧讓留守鄄城的程昱利用自己的威望,先後到範、東阿兩城,安定那裏的軍心,激勵將士們堅守城池,從而保存了三城,使曹操有了反擊呂布的立足之地。

荀彧
陶謙死後,曹操打算乘機再伐徐州。荀彧認爲應當先平定呂布,如果舍呂布而東伐,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足應敵。如果呂布乘虛而入,民心益危,兖州不保。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徐州打不下來,又失去兖州,將會陷入進退失據的險境。荀彧穩定兖州,緩討徐州的方針,爲曹操日後徹底打敗呂布奠定了基礎。
曹操穩定兖州、豫州後,北有袁紹威脅,東有呂布之患,西有關中與袁紹聯合之憂。荀彧爲曹操制定了“討呂布,穩關中,定徐州,戰袁紹”的方針。具體做法是:派鍾繇前往關中,對韓遂、馬超撫以恩德,爭取關中最強勢力,破滅袁紹爭取關中的希望;然後著力攻打呂布,平定徐州,解除東、西兩面的顧慮,形成全力對付袁紹的戰略態勢。
在與袁紹官渡對峙時,曹操因爲軍糧漸漸吃緊,打算退兵回到許昌。荀彧知道後提出反對意見,說:“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官渡大勝後,曹操欲因袁紹新破,以其間擊討劉表。荀彧說:“今紹敗,其衆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遠師江、漢,若紹收其余燼,承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這兩個建議得到了曹操的高度重視,也得到曹操的高度評價:“昔袁紹侵入郊甸,戰于官渡。時兵少糧盡,圖欲還許,書與彧議,彧不聽臣。建宜住之便,恢進討之規,更起臣心,易其愚慮,遂摧大逆,覆取其衆。此彧睹勝敗之機,略不世出也。及紹破敗,臣糧亦盡,以爲河北未易圖也,欲南討劉表。彧複止臣,陳其得失,臣用反斾,遂吞凶族,克平四州。向使臣退于官渡,紹必鼓行而前,有傾覆之形,無克捷之勢。後若南征,委棄兖、豫,利既難要,將失本據。彧之二策,以亡爲存,以禍致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也。”

荀彧
荀彧的這兩個建議被曹操評價爲“睹勝敗之機,略不世出”,“以亡爲存,以禍致福”,可見對曹操的幫助有多大。
上述種種都是荀彧以自己的智慧助力曹操的成功,可以說荀彧對曹操力量的壯大是有大貢獻的。但是同時也可以發現,荀彧的貢獻主要集中在幫助曹操掃除割據勢力統一黃河流域方面。荀彧爲什麽要幫助曹操壯大勢力掃除割據?荀彧、曹操之間的合作關系表象下,有沒有暗地較量?
荀彧與曹操不同的政治訴求荀彧是東漢名門之後,其祖父荀淑是當時名賢李固、李膺的老師。父親荀绲是“荀氏八龍”之一。荀淑的侄子荀昱、荀昙,皆正身疾惡,志除閹宦。荀昱因參與大將軍窦武謀誅宦官,與李膺同時被殺,荀昙也被禁锢終身。荀彧的叔父荀爽也因與黨人關系密切而遭十余年的禁锢,可見荀氏家族是東漢末年黨人的骨幹力量。
黨人是東漢末期興起的以官僚士大夫爲主的政治力量,他們的目的是讓風雨飄搖的朝廷免于崩潰。作爲荀氏家族的後代,荀彧也具有相當濃厚的黨人情結。《後漢書》稱,荀彧“明有意數,見漢室崩亂,每懷匡佐之義”。“匡佐”即挽救輔佐,挽救漢室免于崩潰,輔佐漢室去亂達治,是荀彧的政治理想與訴求。然而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這種品格決定了他必定不能靠自身的力量實現政治理想,必須依靠一個傑出的政治家所領導的軍事集團。因此,荀彧選擇了曹操。
荀彧選擇曹操,首先是因爲曹操的名聲。東漢末期,人物品評大行其道,善于觀察臧否人物的清議領袖對人物的品評,使得一些人才脫穎而出,名聲大振。許劭評價曹操爲“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南陽襄鄉人何颙見過曹操後說:“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李膺的兒子李瓒臨死前對兒子說:“時將亂矣,天下英雄無過曹操。張孟卓與吾善,袁本初汝外親,雖爾勿依,必歸曹氏。”太尉橋玄見到曹操後說:“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可見在東漢末年士人眼中,曹操是英雄,是他們寄托安定漢家天下的希望所在。

曹操
荀彧選擇曹操,其次是因爲曹操的表現。漢靈帝光和末年,曹操任騎都尉時,討伐黃巾軍有功。任濟南相時,罷免大批阿附貴戚、髒汙狼藉的縣吏,濟南國中出現“奸宄逃竄,郡界肅然”的局面。董卓之亂起,曹操拒絕了董卓骁騎校尉之任,間行東歸,在陳留散家財,合義兵,討伐董卓。在所有關東各路討董諸侯中,曹操是最堅定最積極的。這些初步表現了曹操的治理才能和安邦志向。
荀彧選擇曹操,還因爲他對曹操和袁紹做了比較。董卓之亂後,曹操和袁紹是最具實力的兩大軍事政治集團。荀彧先在冀州被袁紹待以上賓之禮,後來,荀彧認爲袁紹最終不能成大事,便離開袁紹投奔了曹操。這一離一就,荀彧是做了認真比較的,他認爲袁紹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曹操明達不拘,唯才所宜;袁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曹操能斷大事,應變無方;袁紹禦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曹操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袁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曹操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爲虛美,行己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吝惜。荀彧把二者的不同歸納爲度、謀、武、德四個方面的差距,成爲他選擇曹操最堅實的基礎。
然而曹操並非平庸志短之輩,他自己說本志只想封侯作征西將軍,死後在墓碑上刻“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就心滿意足了,實際並非如此。曹操心高志大,有三件事非常典型。第一件事,曹操在參加袁術母親的葬禮時,遇到了好友汝南人王儁。曹操看著袁紹、袁術兄弟,小聲對王儁說:“天下將亂,爲亂魁者必此二人也。欲濟天下,爲百姓請命,不先誅此二子,亂今作矣。”王儁說:“如卿之言,濟天下者,舍卿複誰?”說完二人相對而笑。第二件事,獻帝遷都許昌後,太史令王立借金星火星交會天象,宣揚革命將發生,漢祚將終,必有新興者代替。甚至對獻帝說:“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漢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曹操聽說後,派人告訴王立說:“知公忠于朝廷,然天道深遠,幸勿多言。”
第三件事,袁紹曾經拿著一枚玉印走到曹操座邊,把印放在曹操肘下,曹操的反應是“笑而惡焉”。 袁紹此舉是在借用一個典故,建武三年(27年) ,涿郡太守張豐起兵反。張豐之所以起兵,是因爲有道士說他當爲天子,並以五彩囊裹石系在他的肘下,告訴他石中有天子玉玺。張豐好方術,信了道士之言,遂起兵反。後來兵敗被俘,被斬前還說“肘石有玉玺”。袁紹把曹操比作想當皇帝的張豐,曹操之“笑”是表面的,爲了淡化事情的嚴重性,而“惡”是內心的,厭惡袁紹看穿了其雄心大志。王儁說曹操是“天下之雄也,必能興霸道,繼桓、文之功者也”,沈友說曹操“有無君之心”,陳壽說曹操是“非常之人,超世之傑”,都准確地反映了曹操的政治追求。
荀彧與曹操的政治訴求有同有異,二人都主張結束分裂天下共主,但誰是“共主”,二人目標則不同。南朝宋裴松之說:“彧豈不知魏武之志氣,非衰漢之貞臣哉?良以于時王道既微,橫流已極,雄豪虎視,人懷異心,不有撥亂之資,仗順之略,則漢室之亡忽諸,黔首之類殄矣。夫欲翼贊時英,一匡屯運,非斯人之與而誰與哉?是故經綸急病,若救身首,用能動于崄中,至于大亨,蒼生蒙舟航之接,劉宗延二紀之祚,豈非荀生之本圖,仁恕之遠致乎?”

曹操
荀彧與曹操共事近二十年,對曹操的政治訴求應當十分清楚,然而在天下分崩、漢室衰微、群豪虎視、人懷異心的情況下,要想實現自己的政治訴求,除了依靠曹操的力量還能依靠誰呢?
荀彧與曹操的智慧較量明知曹操不是衰漢之貞臣,卻還必須依靠他實現自己的政治訴求,這是一對顯而易見的矛盾。爲使這對矛盾統一起來,荀彧采取了三種策略。
策略一:給曹操的行爲戴上道德的高帽,用道德對曹操進行規範。例如對曹操迎獻帝之舉,荀彧說:“昔漢高祖東伐爲義帝缟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難于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醫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轸,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爲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爲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
曹操迎獻帝都許,是“奉天子以令不臣”,重點是“令”,即以天子之名號令天下。而荀彧則把此舉譽爲心在王室、存本之義、順從民望、秉持至公、扶持弘義等一系列美德,欲從道德方面規範迎獻帝的行爲。
策略二:給曹操的某些越軌的打算設置障礙,使其難以逾越。 例如建安九年(204年),曹操攻破邺城後,自領冀州牧。這時候,有人建議“宜複古置九州,則冀州所制者廣大,天下服矣”。這個建議是否曹操授意提出的史無明確記載,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這絕對是對鞏固擴大曹操勢力有利的“複古”措施。元胡三省說曹操行古九州制度,是“欲廣其所統以制天下耳”。清趙翼說曹操行古九州制度是“自爲張本,欲盡以爲將來王畿之地故也”。今人顧颉剛、史念海說曹操“恢複九州者,不過假其名以益冀州之土地”。趙凱也指出:“顯然,曹操恢複《禹貢》九州的真正目的在于擴大冀州地盤,把‘大冀州’作爲自己的根據地。”這些雖然是對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恢複古九州的評論,但完全適用于建安九年(204年)的情形。荀彧顯然不願意曹操的根據地極度擴張,因此提出反對意見:“今若依古制,是爲冀州所統,悉有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並之地也。公前屠邺城,海內震駭,各懼不得保其土宇,守其兵衆。今若一處被侵,必謂以次見奪,人心易動,若一旦生變,天下未可圖也。願公先定河北,然後修複舊京,南臨楚郢,責王貢之不入。天下鹹知公意,則人人自安。須海內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

荀彧
荀彧反對複古九州制度,實質上是不願意曹操的勢力不受限制地發展,但表面理由是爲了安定天下人心,有利于社稷長久,使得曹操沒有拒絕的理由。曹操複古九州制度是在荀彧死後第二年才加以實施,可見荀彧有效地阻止了曹操擴大根據地的意圖。
建安十七年(212年),董昭等人建議進曹操爲魏國公,行九錫之賜,用以表彰曹操所立功勳。 根據王莽代漢的經驗,行九錫之賜意味著改朝換代的前奏。 因此,荀彧是萬萬不能同意的。“彧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雖勳庸崇著,猶秉忠貞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言外之意,如果行九錫之賜,曹操就違背了匡朝甯國的宗旨,就是喪失了對朝廷的忠貞,就是陷曹操于不義。荀彧以維護曹操忠貞大義名節盛德爲由,使得曹操不得不暫時放棄行九錫的打算。
策略三:向曹操舉薦與自己關系密切的人。荀彧曾向曹操推薦一批人才,他們有荀攸、鍾繇、陳群、司馬懿、郗慮、華歆、王朗、荀悅、杜襲、辛毗、趙俨、戲志才、郭嘉、杜畿等。這批人分兩種情況:有的與荀彧同鄉同郡,如鍾繇、陳群、杜襲、辛毗、趙俨、郭嘉都是颍川人。他們大多與荀彧關系密切,荀攸是荀彧的從子,關系之親密自不待言。鍾繇十分看重荀彧,說顔淵之後,能備九德不二其過的人,只有荀彧。 司馬懿說:“百數十年間,賢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有的與曹操開始關系並不密切,到後來成爲曹操集團中卿相才臣,如郗慮、陳群、王朗、杜畿等人。郗慮是孔融的故吏,曹操說他與郗慮“亦無恩紀”,可見荀彧開始是作爲自己的同盟者向曹操舉薦郗慮的。
陳群是荀彧的女婿,又與孔融是摯友。孔融高才倨傲,年紀在陳群與其父陳紀之間。孔融先與陳紀爲友,後來與陳群交友後,自動把自己降一輩。孔融“志在靖難”,知曹操“終圖漢室,不欲與同”,這點與荀彧十分相似,作爲孔融的好友,陳群的感情天平也應當偏向荀彧。可見荀彧推薦陳群的動機恐怕與推薦郗慮相同。
王朗開始也與曹操關系疏遠,有幾件事可以證明。陳留人邊讓,東漢末被大將軍何進征召,孔融、王朗時爲大將軍府掾,一起“修刺候焉”。邊讓、孔融都因對曹操多輕侮之言而被殺,王朗與他們意趣相投,可證其初期對曹操的態度。沛國名士劉陽與王朗交友。劉陽認爲曹操是朝廷大患,意欲除之。劉陽死後,曹操四處搜捕他的兒子,劉陽的親舊無人敢藏,而王朗卻隱藏他多年。

王嚴
王朗任會稽太守時,迫于孫策的軍事壓力而投降。由于荀彧舉薦,曹操以朝廷名義征召之,于是王朗輾轉江海,來到北方。“太祖請同會,啁朗曰:‘不能效君昔在會稽折粳米飯也。’朗仰而歎曰:‘宜適難值!’太祖問:‘雲何?’朗曰:‘如朗昔者,未可折而折;如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也。’”“可折而不折”是指曹操當入朝觐見皇帝而不入朝。 可見王朗初入朝廷與荀彧、曹操關系的親與疏。
京兆杜陵人杜畿與荀彧的關系更耐人尋味,史載:“畿自荊州還,後至許,見侍中耿紀,語終夜。尚書令荀彧與紀比屋,夜聞畿言,異之,旦遣人謂紀曰:‘有國士而不進,何以居位?’既見畿,知之如舊相識者,遂進畿于朝。”與杜畿一見如故終夜徹談的侍中耿紀,在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曾經與太醫令吉本、司直韋晃共同發動了反對曹操的政變。當然這並不是說杜畿和耿紀初見時的徹夜長談是針對曹操,但耿紀的政變是其長期堅持尊奉漢朝的結果。杜畿和耿紀長談的內容當是如何興複漢朝。這也正符合荀彧的政治訴求,所以“夜聞畿言”之後稱之爲國士。 見到杜畿“知之如舊相識者”,亦見他舉薦杜畿的動機。
荀彧所舉薦的人還有辛毗、杜襲、趙俨,他們都是荀彧的同鄉,而且和陳群同樣知名,“號曰辛、陳、杜、趙”。從荀彧與陳群的關系推測推其舉薦辛毗、杜襲、趙俨的動機也並非毫無根據。
綜上所述,荀彧雖然給曹操的統一北方行動以巨大幫助,但由于二人的政治訴求不同,荀彧又企圖通過自己的辦法,把曹操的政治發展納入自己設定的軌道。作爲有豐富政治經驗的曹操當然不會就範。對于道德約束,曹操曆來采取實用主義,即于己有利者遵之,于己不利者棄之。 例如曹操建安十五年(210年)所發的求賢令:“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于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同年底,他又發布了《讓縣自明本志令》:“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爲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爲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違迕諸常侍。以爲強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去官之後,年紀尚少,顧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爲老。內自圖之,從此卻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裏,于谯東五十裏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後征爲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多兵意盛,與強敵爭,倘更爲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後還到揚州更募,亦複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領兖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又袁術僭號于九江,下皆稱臣,名門曰建號門,衣被皆爲天子之制,兩婦預爭爲皇後。志計已定,人有勸術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後孤討禽其四將,獲其人衆,遂使術窮亡解沮,發病而死。及至袁紹據河北,兵勢強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但計投死爲國,以義滅身,足垂于後。幸而破紹,枭其二子。又劉表自以爲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卻,以觀世事,據有當州,孤複定之,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今孤言此,若爲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強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況燕後嗣乎!’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余萬,其勢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讀此二人書,未嘗不怆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以及子桓兄弟,過于三世矣。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常以語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謂之言:‘顧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欲令傳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懇懇敘心腹者,見周公有《金縢》之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己離兵爲人所禍也。既爲子孫計,又己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爲也。前朝恩封三子爲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複以爲榮,欲以爲外援,爲萬安計。孤聞介推之避晉封,申胥之逃楚賞,未嘗不舍書而歎,有以自省也。奉國威靈,仗钺征伐,推弱以克強,處小而禽大。意之所圖,動無違事,心之所慮,何向不濟,遂蕩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謂天助漢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曹操說有人見他日益強盛,私下議論他有“不遜之志”,恐怕不是捕風捉影的猜測。有人勸他爲避免“不遜”之嫌,把兵權交還皇帝,曹操予以堅決拒絕,稱自己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表示絕不會被道德虛名所累而使自己處于危險境地。

荀彧
對于荀彧的設置障礙,曹操則根據具體情況靈活應對。例如建安九年(204年),曹操自領冀州牧後,想據《禹貢》恢複古代大冀州制度。荀彧反對,曹操采取了退讓態度。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當時袁紹殘余還在,北方尚未平定,關中也各自爲政,荊州劉表收留了劉備,二人聯手曾一度推進到宛縣、葉縣一帶。在這種情況下,曹操仍需要荀彧這樣的人出謀劃策。但這種退讓是暫時的隱忍,建安十七年(212年)曹操欲行九錫之禮,荀彧反對,曹操便不能容忍了,不但逼死了荀彧,而且相繼把行九錫和大冀州計劃付諸實施。
曹操花大氣力對付的是把荀彧推薦的一批人化疏爲親。荀彧曾向曹操推薦了一批人才,這些人絕大部分起初是荀彧的同盟者,然而後來卻一個個成爲曹操集團的政治骨幹。華歆和郗慮曾奉曹操之命進入皇宮搜捕伏皇後,荀攸、鍾繇、王朗、杜襲、郗慮都是曹操加九錫的推手,辛毗、陳群、華歆、王朗都是擁戴曹丕代漢的功臣。這些人的變化,曹操應當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由于材料所限,有些人的記載只有轉變的結果,有些人的記載不但有轉變的結果,而且也能看到曹操爲這種轉變付出的蛛絲馬迹。
郗慮年少時師從于大儒鄭玄,又是孔融的故吏,起初和孔融關系不錯。曹操迎獻帝定都許昌,孔融推舉郗慮,盛贊其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又明《司馬法》,郗慮也稱孔融奇逸博聞。後來兩人發生矛盾,據虞溥《江表傳》載:獻帝曾同時接見郗慮和孔融,問孔融說:“鴻豫何所優長?”孔融答:“可與適道,未可與權。”郗慮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人流,其權安在?”于是兩人互相比較長短,以至不睦。曹操本來就不滿孔融與自己離心離德,正好利用這種矛盾爭取郗慮。史載“山陽郗慮承望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郗慮所秉顯然是曹操之風旨,從而導致孔融因小小的過錯被免官,二人仇怨也因此公開。 曹操又給孔融寫信說:“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後世德薄,猶有殺身爲君,破國爲國。及至其敝,睚眦之怨必仇,一餐之惠必報。故晁錯念國,遘禍于袁盎;屈平悼楚,受谮于椒、蘭;彭寵傾亂,起自硃浮;鄧禹威損,失于宗、馮。由此言之,喜怒怨愛,禍福所困,可不慎與!昔廉、蔺小國之臣,猶能相下;寇、賈倉卒武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伯升之怨;齊侯不疑射鈎之虜。夫立大操者,豈累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以爲小介,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怃然,中夜而起。昔國家東遷,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于鄭玄,又明《司馬法》,鴻豫亦稱文舉奇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違。孤與文舉既非舊好,又于鴻豫亦無恩紀,然願人之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君群小所構,孤爲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爲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余矣。”
信中通篇引用典故,除去這些典故,主要講了三個意思:第一,要孔融效法唐虞時代的克讓之臣,不要學後世睚眦之怨必仇的德薄表現。第二,郗慮上表是出于公法,而個人私情是芥蒂小事,當放棄芥蒂秉持公法,不應怨毒漸積,志相危害。第三,當初互相擡舉,如今與始相違,當是虛僞狡猾的小人所構。這封信批評、歸咎孔融,爲郗慮開脫辯護的傾向非常明顯。《後漢書》上說,曹操這封信是“激厲”孔融。這裏的“激厲”絕無今日“鼓勵”“勉勵”之意,而是用較激烈的語言對孔融進行勸誡。
孔融的回信中有“知同其愛,訓誨發中”之語,意思是知道曹操像愛護郗慮一樣愛護自己,所以才對自己有衷心的訓誨。這實際上是表達了對偏袒郗慮的不滿。他雖然表示要與郗慮“修好如初”,對曹操的“苦言至意,終身誦之”,但實際上並未與郗慮改善關系,後來郗慮再一次構成孔融的罪過,給曹操殺掉孔融提供借口。從郗慮與孔融的交惡中,可見曹操對郗慮的偏袒與拉攏。

鍾繇
曹操對鍾繇的爭取有兩個方面的線索。一個是對鍾繇的寬容。曹操在徐州、冀州一帶拓展勢力的時候,關中地區馬騰、韓遂等,各擁強兵相與爭。爲穩定關中,曹操派鍾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委之以後事,特使不拘科制。在此期間,發生了河東太守王邑、郡掾衛固、中郎將範先等抗旨事件。王邑因違反朝廷法律,被責令交出印绶,回朝廷等候發落。與此同時,曹操又任命杜畿爲河東太守取代王邑。杜畿已經進入河東郡界,而王邑拒不交出印绶,而是自己帶著印绶到許昌投案。王邑的部下衛固、範先起兵拒絕杜畿上任。鍾繇時治在洛陽,自以威禁失督司之法,乃上書自劾:“臣前上言故鎮北將軍領河東太守安陽亭侯王邑巧辟治官,犯突科條,事當推劾,檢實奸詐。被诏書當如所糾。以其歸罪,故加寬赦。又臣上言吏民大小,各懷顧望,謂邑當還,拒太守杜畿,今皆反悔,共迎畿之官。謹案文書,臣以空虛,被蒙拔擢,入充近侍,兼典機衡,忝膺重任,總統偏方。既無德政以惠民物,又無威刑以檢不恪,至使邑違犯诏書,郡掾衛固诳迫吏民,訟訴之言,交驿道路,漸失其禮,不虔王命。今雖反悔,醜聲流聞,咎皆由繇威刑不攝。臣又疾病,前後曆年,氣力日微,屍素重祿,曠廢職任,罪明法正。謹按侍中守司隸校尉東武亭侯鍾繇,幸得蒙恩,以鬥筲之才,仍見拔擢,顯從近密,銜命督使。明知诏書深疾長吏政教寬弱,檢下無刑,久病淹滯,衆職荒頓,法令失張。邑雖違科,當必繩正法,既舉文書,操彈失理,至乃使邑遠詣阙廷。隳忝使命,挫傷爪牙。而固诳迫吏民,拒畿連月,今雖反悔,犯順失正,海內凶赫,罪一由繇威刑闇弱。又繇久病,不任所職,非繇大臣當所宜爲。繇輕慢憲度,不畏诏令,不與國同心,爲臣不忠,無所畏忌,大爲不敬。又不承用诏書,奉诏不謹。又聰明蔽塞,爲下所欺,弱不勝任。數罪謹以劾,臣請法車征詣廷尉治繇罪,大鴻胪削爵土。臣久嬰笃疾,涉夏盛劇,命縣呼吸,不任部官。辄以文書付功曹從事馬適議,免冠徒跣,伏須罪誅。”
鍾繇的自我彈劾反映了事件的嚴重性,然而曹操對此的反應是“ 诏不聽”,對鍾繇未加以任何處罰。另一個是通過兒子曹丕拉近與鍾繇的關系。曹丕與鍾繇交往密切,鍾繇任魏國相國,作爲魏太子的曹丕便賜給鍾繇一個五熟釜,釜上鑄有銘文說:“于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實幹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僚師師,楷茲度矩。”稱贊鍾繇作爲相國,忠心輔佐魏國,實爲百僚楷模。 他還給鍾繇寫信說:“昔有黃三鼎,周之九寶,鹹以一體使調一味,豈若斯釜五味時芳?蓋鼎之烹饪,以飨上帝,以養聖賢,昭德祈福,莫斯之美。故非大人,莫之能造;故非斯器,莫宜盛德。今之嘉釜,有逾茲美。夫周之屍臣,宋之考父,衛之孔悝,晉之魏顆,彼四臣者,並以功德勒名鍾鼎。今執事寅亮大魏,以隆聖化。堂堂之德,于斯爲盛。誠太常之所宜銘,彜器之所宜勒。故作斯銘,勒之釜口,庶可贊揚洪美,垂之不朽。”
鍾繇有一塊玉玦,曹丕欲得之而羞于開口,私下派曹植托人向鍾繇轉達慕玦之意。鍾繇立即派人給曹丕送去。曹丕寫信給鍾繇表達自己的喜悅之情:“近見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抃俱。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轉言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稱,邺騎既到,寶玦初至,捧跪發匣,爛然滿目。猥以矇鄙之姿,得觀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台之觀,而無蔺生詭奪之诳。嘉贶益腆,敢不欽承!”鍾繇回信說:“昔忝近任,並得賜玦。尚方耆老,頗識舊物。名其符采,必得處所。以爲執事有珍此者,是以鄙之,用未奉貢。幸而纡意,實以悅怿。在昔和氏,殷勤忠笃,而繇待命,是懷愧恥。”
九月九日又稱“重陽”,是當時一個重要節日。九月時值季秋,古人稱之爲“無射”之月,意思是此月陰氣正盛,陽氣極衰,萬物盡滅。在此百花肅殺之際,菊花卻傲霜獨放,因而受到人們的推崇。因此九月九日又有采菊相贈之俗。魏文帝曹丕于九月九日曾贈菊給鍾繇,並附信說:“是月律中無射,言群木庶草無有射地而生。于芳菊紛然獨秀,非夫含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思餐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賜釜、贈玦、送菊花、通書信,曹丕和鍾繇關系的密切,也日益拉近鍾繇與曹操的關系。
曹操通過曹丕交友而使人才靠近自己,不僅是鍾繇,還有荀攸、陳群等人。曹丕爲魏國太子,曹操對曹丕說:“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荀攸曾經有病,曹丕前去探望,對荀攸“獨拜床下”,表現出格外尊敬。曹丕對陳群也“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禮”,常感歎說:“自吾有回,門人日以親。”據《史記》 載,顔回英年早逝,孔子哭之恸,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裴骃《集解》引王肅曰:“顔回爲孔子胥附之友,能使門人日親孔子。”這裏曹丕借用孔子的話,表達了以有陳群這個朋友爲自豪的感情。曹丕與這些人的友誼日深,爲這些人在感情和思想上與曹操進一步靠攏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荀攸
曹操通過上述努力,逐漸把荀彧最初推薦給他的一批人才化疏爲親,成爲自己雄圖大業的得力助手。最典型者是荀彧的從子荀攸,最後竟然成爲曹操“進爵國公,九錫備物”的擁護者。建安十七年(212年),曹操征孫權,表請荀彧勞軍于谯,便自作主張把荀彧留在軍中,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 曹操軍至濡須,荀彧因病留在壽春,以憂薨。致荀彧之死的憂郁,《魏氏春秋》的記載耐人尋味:“太祖饋彧食,發之乃空器也,于是飲藥而卒。”曹操給荀彧無食物的空飯盒,意味著告訴荀彧,其所推薦的所有人都已經背棄初衷,其圖謀落空了。荀彧感到自己如同這個空飯盒一樣,身邊空無一人,因此在絕望中飲藥自盡。
荀、曹關系與東漢末政治勢力的消長三國孫吳薛瑩在《漢紀贊》中評論東漢末期的局勢說:“漢氏中興,至于延平而世業損矣。沖質短祚,孝桓無嗣,母後稱制,奸臣執政。孝靈以支庶而登至尊,由蕃侯而紹皇統,不恤宗緒,不祗天命,上虧三光之明,下傷億兆之望。于時爵服橫流,官以賄成,自公侯卿士,降于皂隸,遷官襲級,無不以貨。刑戮無辜,摧撲忠賢,佞谀在側,直言不聞。是以賢智退而窮處,忠良擯于下位,遂至奸邪蜂起,法防隳壞,夷狄並侵,盜賊麋沸,小者帶城邑,大者連州郡。編戶騷動,人人思亂。當斯之時,已無天子矣。”
東漢王朝至和帝、殇帝後便開始衰落,到靈帝時達“已無天子”的程度。 所謂“無天子”並非真的沒有了皇帝,而是沒有了天子的權威。天子權威的喪失,象征著王朝的末日。面對這種情況,人們呈現出不同的態度,不同的態度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勢力。
一種政治勢力認爲漢德已亡,新朝當立。民間這種勢力的代表是張角領導的黃巾起義,打出“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旗號。割據諸侯勢力的代表有劉焉、袁術等人。東漢末,朝綱崩壞,太常劉焉要求作交阯牧,後來,侍中董扶對他說:“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劉焉便改牧益州。劉焉在益州“撫納離叛,務行寬惠,陰圖異計”,造作乘輿車具千余乘,並謀劃攻打長安,代漢野心昭然若揭。
袁術也是如此。當時流行一句谶語:“代漢者當塗高。”塗即路也,袁術字公路,名和字與谶語合,他認爲:“今海內鼎沸,劉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祿去漢室久矣,天下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割疆宇。此與周末七國無異,唯強者兼之耳。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所以在建安二年(197年),袁術借符命在九江稱帝,自稱“仲家”。以九江太守爲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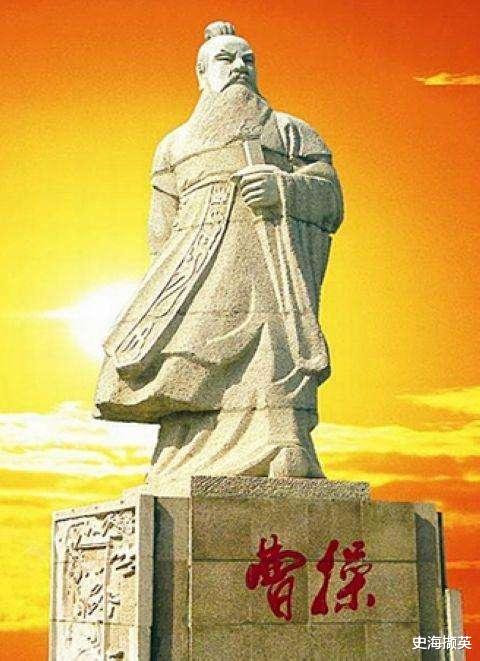
曹操
另一種政治勢力認爲漢德已衰,天命將改。漢德已衰則失去對漢朝重振的希望,天命將改則預示了天命必改的趨勢。他既區別于天命依然眷顧漢朝,從而對朝廷表現出絕對的忠誠,也不同于天命當改從而建號稱帝,而是看到即將改朝換代的趨勢,從而認定皇帝還有暫時存在的價值。突出代表就是曹操,典型做法就是“挾天子以令諸侯”。
還有一種政治勢力認爲漢德雖衰,天命未改。這些人是欲使東漢起死回生的忠臣,雖然社會到了“主荒政謬”“編戶騷動,人人思亂”的地步,而他們卻仍“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如漢桓帝時,朝政已經腐敗,而尚書令陳蕃仍向朝廷舉薦徐稺、姜肱、袁闳、韋著、李昙等五位德行純備的處士,希望他們“協亮天工”,“翼宣盛美,增光日月”。
漢靈帝光和七年(184年) 爆發了黃巾起義,左中郎將皇甫嵩因鎮壓黃巾起義有功被賜爵封侯,威震天下。 一個當過信都令名叫閻忠的人對皇甫說:“身建不賞之功,體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皇甫嵩說:“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閻忠說:“夫既朽不雕,衰世難佐。若欲輔難佐之朝,雕朽敗之木,是猶逆坂走丸,迎風縱棹,豈雲易哉?且今豎宦群居,同惡如市,上命不行,權歸近習,昏主之下,難以久居,不賞之功,讒人側目,如不早圖,後悔無及。”皇甫嵩拒絕說:“人未忘主,天不祐逆。若虛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禍,孰與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雲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論,所不敢聞。”範晔說皇甫嵩“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眄,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劄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

傅燮
曾和皇甫嵩一起鎮壓黃巾的傅燮,後來被排擠,到漢陽郡任太守。金城人王國聯合北地胡攻打郡城,他的兒子傅幹說:“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于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裏羌胡先被恩德,欲令棄郡而歸,願必許之。徐至鄉裏,率厲義徒,見有道而輔之,以濟天下。”傅燮說:“汝知吾必死邪?蓋‘聖達節,次守節’。且殷纣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稱其賢。今朝廷不甚殷纣,吾德亦豈絕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死于此。”最後戰死。
上述東漢三種政治勢力,第一種由于不符合社會實情,遇到重重阻力,很快就敗下陣來。第二種是對東漢末期社會政治及未來走向的深入觀察和正確判斷,因而力量由小變大,由弱到強。第三種是欲挽狂瀾,卻無力回天,除了以身殉名節,沒有取得絲毫實質性功業。荀彧是第三種政治勢力的傑出代表。說他傑出,是他與陳蕃、皇甫嵩、傅燮等人不同,認識到憑一己之力不能扶大廈于將傾,而是試圖借助強大的勢力實現自己的政治訴求。這是他比其他人聰明之處。然而其聰明並不能挽救失敗的命運,荀彧的死既意味著其政治訴求的失敗,也證明了任何想借助別人的力量實現自己的目的都是徒勞的。
荀彧與曹操的關系並非像有論者所說是主從關系,是有共同理想長期主倡臣隨的關系,而是一種既合作又較量的關系。這種關系是二人的政治訴求有同有異所決定的。結束分裂天下共主是二人的同,誰做共主是二人的異。荀彧需要借助曹操的力量達到自己的政治訴求,同樣,曹操也需要借助荀彧的智慧實現自己的目的。因此二人較量是合作下的較量,不具有你死我活的性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