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歡京劇的朋友可能知道,形容京劇的劇目之多,有一句話叫“唐三千·宋八百(讀如‘伯’),數不清的三列國”。意思是說,京劇中春秋列國、三國、唐、宋的曆史戲占了大頭。宋代八百出戲,看起來比唐代少很多,但知名度較之唐代卻遠甚,《三打陶三春》《打黃袍》《狸貓換太子》《鍘美案》,不僅是京劇的經典劇目,也因爲各式各樣的“包青天”而走紅。
其實,不止京劇,以宋朝爲背景的小說或戲劇,比如人人皆知的《水浒傳》,還有不那麽爲人熟知的《王魁負桂英》,近年來的賺足眼球的《知否》《清平樂》,在當時、後世,乃至現在都是“流量”。
這些故事中的人物身份各異,或是異姓王,或是太後,或是驸馬,或是天上星宿,或是當朝狀元,或是勳戚,或是皇後、公主,其實都圍繞著一個中心展開,那就是皇帝,在當時的語境中,被呼爲“官家”。
在下文中,作者圍繞宋史學者吳铮強的新作《官家的心事:宋朝宮廷政治三百年》一書,從皇權的傳承與後宮政治角度聊聊那些“宋朝官家的心事”。

撰文|馮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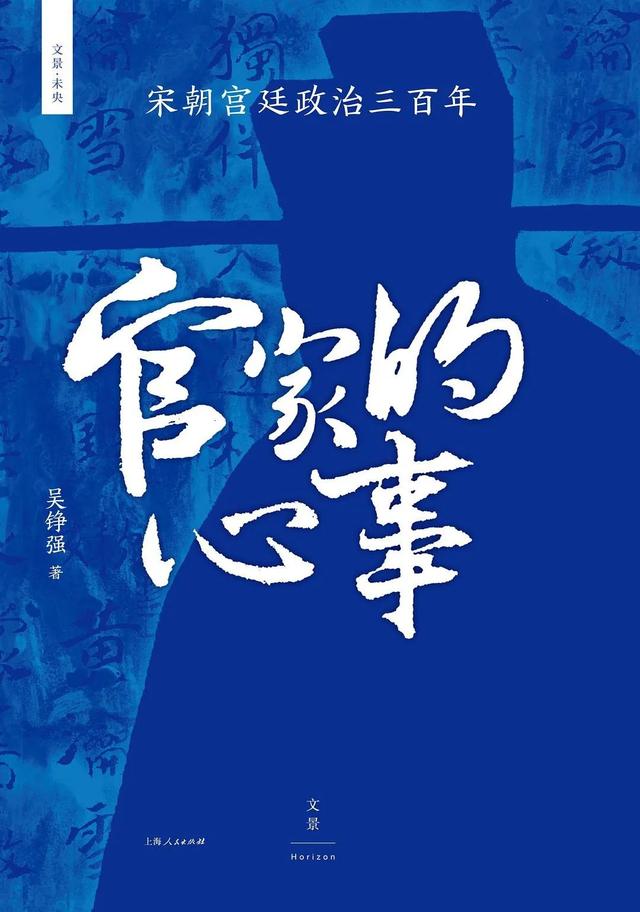
《官家的心事:宋朝宮廷政治三百年》,吳铮強著,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年10月。
宋代政治的核心問題
官家這個稱呼,最早見于《晉書·石季龍載紀》,後趙武帝石虎之子石邃欲弑父篡位,他說:“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鑒》時,將此事系于晉成帝元康三年,元代史學家胡三省對此的注釋是:“稱天子爲官家,始見于此。西漢謂天子爲縣官,東漢謂天子爲國家,故兼而稱之。或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故兼稱之。”從兼稱的角度理解這個詞,胡三省實際上是在尋找史源依據,這是沒錯的。
其實,胡三省的話並不是他自己從史書中發見而來,而是前人已經有說。據王君玉《國老談苑》記載:“徐铉爲散騎常侍,太宗謂曰:‘官家’之稱,其義安在?铉曰: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蓋皇帝之謂也。”又文瑩的《湘山野錄》記載,宋真宗酒量很好,近臣難有可與匹敵者,聽說侍讀學士李仲容號稱海量,就起了較勁的心思。“一夕,真宗命巨觥俾滿飲,欲劇觀其量,引數入聲。大醉,起,固辭曰:告官家撤巨器,上乘醉問之:何故謂天子爲官家?遂對曰:臣嘗記蔣濟《萬機論》言,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上甚喜。”
不過,宋代最早稱皇帝爲官家的,既不是太宗,也不是真宗,而是趙匡胤自己,宋代王鞏的《聞見近錄》記載:
太祖即位,方鎮多偃蹇,所謂“十兄弟”者是也。上一日召諸方鎮,授以弓劍,人馳一騎,與上私出固子門,大林中下馬,酌酒,上語方鎮曰:“此處無人,爾輩要作官家者,可煞我而爲之。”方鎮伏地戰恐,上再三喻之,伏地不敢對。上曰:“爾輩是真欲我爲主耶?”方鎮皆再拜,稱萬歲。上曰:“爾輩既欲我爲天下主,爾輩當盡臣節,今後無或偃蹇。”方鎮複再拜,呼萬歲,與飲盡醉而歸。
這個故事在《聞見近錄》中正接“杯酒釋兵權”故事之下,可以看成是同一個事件的不同版本。宋代像這樣關于皇帝在宮闱中的故事非常多,而一事之間近似或者矛盾的記載更是常見,諸正史、筆記,還有《長編》所彙集的各種資料可能對一事有數種記載。這些資料對于同一件事的記載紛繁複雜,如何從不同側面對其進行利用、辨析、推論,都爲探討兩宋時代宮廷政治提供了廣泛的可能性。

(明)劉俊 《雪夜訪普圖》軸(局部),描繪宋太祖雪夜訪趙普的曆史故事。
宮廷政治曆來是人們關注的熱點,因爲官家事至大而隱秘,距離老百姓又遠,事大而隱秘故能發揮,距離遠則不至于立時招來災禍。它不僅是民間茶余飯後的談資,也是文學創作的富礦,更是學者研究的一大熱點。吳铮強教授的《官家的心事》(下文中簡稱“吳書”),就是最近大量利用筆記、《長編》研究宋代宮廷政治的著作。
《官家的心事》的書名就已經點明了其研究對象是以皇帝爲核心的宮廷政治,在書的背面有一句話叫“不研究宮廷政治,就讀不懂宋史”,這句話不僅適用于宋代,而且適用于整個中國古代帝制社會。因爲皇帝制度是中國古代帝制社會最核心最重要的制度,而宮廷又是皇帝制度中,涉及皇帝日常生活的場域,其中不僅有宮廷的制度,還有政治中的人性。雖然王者無私,但人性複雜,涉及至高權力時,人性的面相就會暴露,這些人性的諸面相透過權力暴露出來,就是赤裸裸的權力鬥爭。從這個角度上來說,研究宮廷政治,可以從隱秘的角落中更好地理解中國古代政治運作,乃至政治中的人性。
全書二十一章,其實細分的話,不過四個部分:皇位傳承、後妃宮鬥、太後聽政、外朝鬥爭,四者之間相互糾葛,共同構成了官家的“心事”。細想起來,確實如此,天子以天下爲家,王者不言私,但繼承人問題,後宮與外朝,確實是官家的“心事”,因爲皇帝權力至高無上,但繼承人涉及到的是皇帝怎樣退出曆史舞台,後宮和外朝則始終是皇權能否得到伸張最直接的對手方,因此關注這些人和事,才能發現官家的“心曲”,進而窺見官家的“心事”。
吳書一出,諸家已經從諸多方面進行了述評,如席缪關注太祖太宗的即位問題與後世《水浒傳》中的人物書寫;虞雲國從各個方面都對吳書進行了評價並加以了肯定。本文擬從皇權的傳承與後宮政治角度,接著吳書談一些問題。
濮議與天子家事
中國古代的《春秋》經傳中,記載有這樣一件事情,公孫嬰齊因爲繼承了其兄公孫歸父的統緒,因此他就不能再稱公孫,而應該以他現在的祖父,也就是他父親的字爲氏,這就是說他應該被稱爲仲嬰齊。這就是《春秋》之義中所謂的“爲人後者爲之子”。小宗入繼大宗,按說應該嚴格遵循這條經義,但原人之心,無不想尊隆其父,因此,中國曆史上緊接著入繼問題的往往就是尊隆皇帝的生父問題。
兩宋時代,由于獨特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形勢,讓繼承人問題變成了一個非常敏感,又特別容易引起皇帝、後宮、前朝鬥爭的問題。吳書中指出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那就是兩宋皇位繼承有某種相似之處,“不知是有意無意,兩宋前五朝的皇位繼承都出現了結構性的相似性,太祖、太宗與高宗、孝宗都是兩大支系之間的傳授,真宗、光宗都以皇三子繼承皇位,仁宗與甯宗都是皇帝的唯一子嗣,英宗與理宗都以旁支入統。”(《官家的心事》305頁,下同)這種結構性的相似性會帶來很多問題,因此,這其中就會産生很多意味深長的故事。

《清平樂》劇照。
衆所周知,宋英宗以旁支(小宗)入繼仁宗,在即位之後的治平元年(1064年),韓琦、歐陽修等奏請尊禮濮安懿王爲皇考。尊禮之事引起與王珪、司馬光、呂誨、範純仁、呂大防、賈黯等台谏大臣的不滿,主張稱濮王爲皇伯。史稱“濮議”之爭。此事件導致呂誨、範純仁、呂大防等人被貶黜。治平三年(1066年),由于宋英宗具有強烈的意願,最終迫使曹太後同意英宗稱濮安懿王和三位妻妾(谯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爲“親”,尊濮安懿王爲皇考濮安懿皇,三位妻妾並尊爲後。英宗下旨,以禮追崇生父和三位夫人,爲其修建陵園和宗廟。但趙允讓一直沒有獲得明確的皇帝尊號,隨著英宗的去世,事情不了了之。
英宗在位時間很短,“濮議”事件也不過前後三年,但此事影響卻大。甚至對高宗、孝宗的皇位傳承問題都有影響,這就不得不從高宗選擇嗣子說起。吳書中已經詳細介紹了“太祖之後當再有天下”一說的來龍去脈,以及高宗對此的反應(291-294頁)。但書中對于高宗爲什麽選擇太祖之後卻語焉不詳,這恐怕還是要從高宗的心態說起。
我們猜測,高宗對“濮議”一定是熟悉且充滿警惕的,這種心態促使高宗要在太祖,而不是太宗-濮王一系中選擇繼承人。南渡之後,宗室保存相對比較完整的只有濮王一支,趙構的族叔祖輩裏有嗣濮王趙仲湜。與其同輩的趙仲儡,曾擔任過知南外宗正事;趙構的叔伯輩裏有濮王的三個兒子趙士從、趙士街、趙士篯,在建炎、紹興年間先後擔任過同知西外宗正事、同知大宗正事;還有同輩的趙士珸擔任過知南外宗正事。另外,太宗-濮王系的趙構叔伯輩中,最有實力的應該是齊安郡王趙士㒟,趙士㒟在靖康末年就已經權知大宗正事,他與孟太後的支持是趙構繼位的最重要原因;苗劉之亂時,又是他密告張浚勤王,救了趙構一命。嶽飛案時,趙士㒟曾上書“臣以百口保飛無他”,可見其家族繁衍之廣。如果選擇濮王趙允讓一系來繼承皇位,高宗很可能遭受仁宗的待遇,甚至由于嗣皇帝的壽數綿長,自己在身後還要下仁宗一等。因此,選擇太宗-濮王一系的後嗣作爲繼承人,並不符合高宗的心理預設。

宋高宗趙構像。
同樣,在選擇太祖一系的繼承人時,也並沒有選擇燕王趙德昭一系,而是選擇了在當時已經幾無規模的秦王趙德芳一系,宋孝宗生父趙子偁,官宣教郎,這是從八品的小官;後來又收養的趙伯玖,其生父趙子彥,官秉義郎,同樣是從八品的小官。唯一不同的就是趙子偁是文官,而趙伯玖是武官。由此觀之,不能不說高宗在選擇繼承人這件事上頗有安排,而這種安排,很可能就是“濮議”對他的潛在影響。選擇弱勢的太祖之後的支系入嗣,能夠最大限度地杜絕“濮議”的産生,也就能夠最大限度地保住自己的體面。一系列隱微複雜操作的背後,可能原因就是如此簡單。
同樣的,高宗在內禅之後也沒有放松對孝宗的控制,除了對皇權的眷戀之外,同樣可能也有“濮議”的影響。高宗在太上皇時期一直在控制、試探孝宗,動辄以“老而不死,爲人所厭”這樣的話“PUA”(pick-up artist,指一種控制對方情緒的交流手段)孝宗,然孝宗處于一種緊張狀態中。如《西湖遊覽志余》記載:
德壽生日,每歲進奉有常數;一日,忽減數項,德壽大怒。孝宗皇懼,召宰相虞允文語之。允文曰:“臣請見而解之。”孝宗曰:“朕立待卿回奏。”允文到宮上谒,德壽盛氣。頃之,曰:“朕老而不死,爲人所厭。”允文曰:“皇帝聖孝,本不欲如此,罪在小臣。謂陛下聖壽無疆,生民膏血有限,減生民有限之膏血,益陛下無疆之聖壽。”德壽大喜,酌以禦醞一杯,因以金酒器賜之。允文回奏孝宗,孝宗亦大喜,酌酒賜金如德壽雲。
高宗對孝宗的這類言論還屢見于其他宋代筆記中,余英時就曾利用精神分析學說對高宗、孝宗的關系進行分析,很能切中問題。不過假如能夠從豐富的材料中考察,似乎也能得出相同的結論。與其說高宗的一系列負氣之言是貫徹其自身的政治意志,不如說都是對並非親生子的孝宗的考驗和試探,孝宗也確實承受著這種壓力,內裏還是對非親生子孝宗的不信任和對自己地位的深層焦慮。而在高宗之後,孝宗希望依樣畫葫蘆,以高宗故事內禅光宗,但事情又朝超過了他預料的方向發展。不過這回是親兒子,事情又不大相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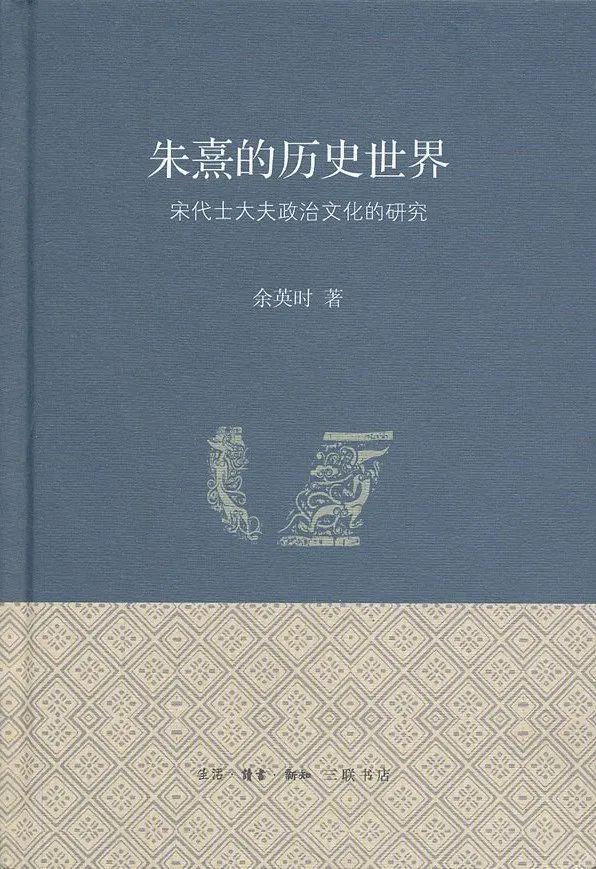
《朱熹的曆史世界》,余英時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1年7月。
前朝與後宮
後宮政治往往幽微難明,但宋代留下的《長編》和各種筆記,讓很多問題的談論有了可能。書中最精彩的是關于真宗劉皇後、仁宗曹皇後和英宗高皇後形象的重新構擬,即書中的第七至十章。讀者可能比較關注作者如何對曆史疑案的邏輯推理,但作者的推理之外,其實還有理論架構滲入其中。無論是劉後、曹後,乃至後來的高後,在作者的筆下其實都有寇准集團的影子;而反觀本書開頭的太祖、太宗之間的皇位繼承問題,實質也是兩大集團之間的鬥爭。這種理論模型的有效性就在于,它能夠將後宮-前朝的關系置于一個非常明晰的框架之內,在此基礎上將問題講清楚,且能夠將許多紛繁複雜的多線條敘事理順,進而呈現作者要給出的答案。前朝與後宮,這在曆史上看似不能有什麽關系的兩者,通過集團論重新走到了一起。
回到後宮的場景中,曹皇後能夠逼迫仁宗至發瘋呓語,乃至自殺的地步,這種說法確實離奇,但事情又確實在情理之中。曹皇後爲了穩定後位的種種手段,確實可能將仁宗逼入死角。其實還應該關注的是作爲後宮政治空間中的皇帝與皇後的身份。吳書指出曹後利用養女爭寵,不過是劉後“借腹生子”的翻版,曹皇後希望將所有仁宗的後嗣都納入到自己的實力範圍之中,這與北魏的“子貴母死”制度最後都權歸太後,在本質上是相同的。又如宮變,吳書充分考慮了宮禁制度和宮廷勢力的分布,認爲這是仁宗爲了拒絕曹皇後侍寢而與張貴妃聯合的一種策略。種種迹象顯示,在宮禁之中,曹皇後已經將仁宗逼入死角。推而廣之來看,皇後完全可以利用宮禁中的特殊空間和制度,將皇帝逼得走投無路。將來,如果結合宋代的禁中的空間格局和宮禁制度,進一步探討宋代的後宮政治,或者還能寫出更受歡迎的作品來,甚至能夠讓影視化取得比《甄嬛傳》更好的效果也說不定。

《清平樂》劇照。
那麽張貴妃和仁宗又是不是“真愛”呢?吳書中指出,後世變法派對張貴妃形象的塑造多半是參考趙飛燕、楊玉環等所謂“紅顔禍水”的形象虛構出來的(150頁),其實這種說法恐顯絕對。王者無私,如果仁宗和張貴妃的聯合是因爲曹皇後的逼迫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那麽張貴妃交通前朝的行爲必然也會受到仁宗的警惕。《邵氏聞見錄》載:
仁宗一日幸張貴妃合,見定州紅甆器,帝堅問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辰所獻爲對,帝怒曰:“嘗戒汝勿通臣僚饋遺,不聽何也?”因以所持柱斧碎之。妃愧謝,久之乃已。
“通臣僚”的行爲大概會讓仁宗不自覺地想起即位初期的章獻,宮闱與外朝的交通,很可能會形成另外一番局面,仁宗要防止産生另一個章獻,就必然對此非常警惕。這也就能理解仁宗怒火中燒的原因。可以說,在聯合張貴妃針對曹皇後的同時,仁宗對張貴妃也有著防範之心,如《聞見錄》中這類記載,可能並非全是汙蔑之辭。
英宗高皇後最值得關注的則是神宗去世之後,到底立子還是立孫的問題。吳書中通過對《長編》中史料的仔細梳理和辨析,得除當時宮廷鬥爭格局的六個方面,其結論是高皇後立哲宗的傾向更大,因爲這樣有利于垂簾聽政(229-230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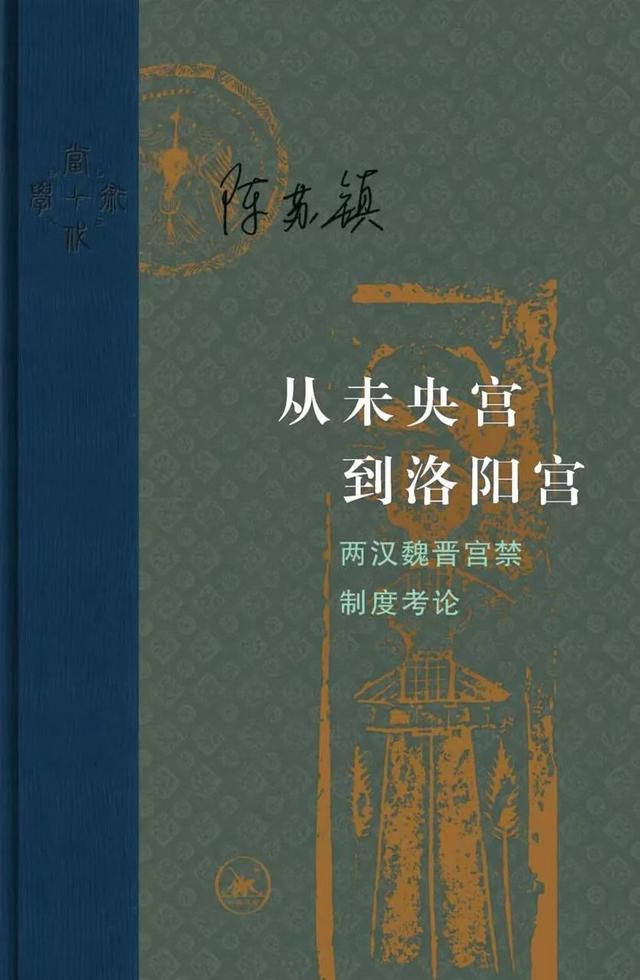
延伸閱讀:《從未央宮到洛陽宮》,陳蘇鎮 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2年8月。
但是,《長編》中所存的異質性材料衆多,如果單單就這些內容而進行邏輯演繹,那麽就顯得危險。如果我們承認那些主要是褒揚蔡確定策之功的材料中有部分的真實性存在,那麽至少我們還能看到當時更加豐富的政治面相。《長編》載《蔡確傳》曰:
元豐六年秋,確與中書侍郎張璪奏事崇政殿,上悲不自勝,謂確曰:“天下事止此矣。”確駭曰:“敢問所因。”上曰:“子幼奈何!”確曰:“陛下春秋鼎盛,忽有不祥之言,不審所謂。”上曰:“天下事,當得長君維持否?”確曰:“延安郡王,陛下長子,臣不知其他,臣有死而已,不敢奉诏。”
這段材料雖然大有擡高蔡確曆史地位的嫌疑,但神宗那句“天下事止此矣”以及“天下事,當得長君維持否”,實在顯示出他的焦慮。在母親強勢的情況下,神宗內心其實也害怕太祖-太宗兄終弟及的情況重演,那麽這時作爲太後的高氏是否有立子而不是立孫的想法,至少是神宗認爲太後有這個想法,就頗微妙了。在這種情況下,作爲後宮母後的高氏其實處于強勢的一方,神宗在身體尚是康強時就已經感受到了強大的心理壓力,此時的後宮,恐怕比史書中記載的更加波雲詭谲。當然,曆史不能假設,最後還是哲宗即位,高氏以太皇太後的身份垂簾,其他所有的內容,都只能是猜測了。
本文爲獨家原創內容。撰文:馮夷;編輯:李永博 朱天元;校對:王心。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