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卿心君悅
康熙四十六年,康熙下旨勒令所有欠款官員,十日內還清欠款,並委派老四胤禛爲追繳國庫欠款的大臣。
期間,部分欠款官員爲了逃避還款,昏招頻出。
有哭窮賣慘的;有撒潑耍橫的;有攀比抵賴的;有煽風點火撺掇別人出頭的,還有拿著家當去前門叫賣的……
而欠了國庫三十五萬兩的魏東亭,在還款無望,限期將至之際,用一條白绫清了債。

初看這段劇情的時候,我一直有個問題沒有想通:
既然魏東亭的欠款,與康熙兩次南巡住在他家有關,且康熙也心知肚明,爲何魏東亭甯願死,也沒向康熙求助呢?
按理說,以康熙的性格,魏東亭真要是求到他面前,無論是出于幾十年的君臣情分,還是出于彌補南巡時魏東亭在他身上的花銷,康熙都不會眼睜睜地看著魏東亭被抄家,大概率會出手相助,魏東亭又何必要以死清債呢?

直到這次重刷《雍正王朝》,看到老十三的那句質問,我才明白,魏東亭甯死也不向康熙開口的背後,到底藏著什麽——有無奈,有取舍,更有赤裸裸的算計。
欠債還錢,天經地義一場突如其來的黃患,撕下了“康熙盛世”的僞裝,也揭開了大清朝官場的醜態。
盛世之下,百萬生民流離失所,朝不保夕,可朝廷卻連赈災修堤的救命錢都拿不出來。
官場之中,王公貴胄們如“官倉鼠”一般,各個肥得流油,堂而皇之的一手向百姓敲骨吸髓,一手從國庫裏掏銀子。

何其諷刺!
真是形象生動又具體的诠釋了曹邺的那首《官倉鼠》:
“官倉老鼠大如鬥,見人開倉亦不走。健兒無糧百姓饑,誰遣朝朝入君口。”
這一次,向來以“仁德”自居的康熙也坐不住了。
在老四胤禛去江南籌款,勉強應付完黃患之後,康熙決定追討官員們從國庫挪借的一千二百萬兩欠款。

起初,對于康熙要追討欠款的旨意,魏東亭是有些不以爲然的。
原因無外乎兩個:
其一,在魏東亭看來,挪借庫銀的人太多,牽扯範圍太廣,甚至涉及到了皇子貝勒,康熙就算想追,也未必下得了決心,很可能只是“幹打雷,不下雨”,喊喊口號罷了。
其二,魏東亭自恃跟著康熙出生入死幾十年,勞苦功高。論資曆,論功績,皇子貝勒見他都是禮待有加,只要不是康熙親自出面,誰也不會拿他這個老臣怎麽樣。
也因此,一些欠款官員們第一次去老八胤祀府上求助時,魏東亭並不在其中。

只不過,魏東亭低估了朝廷追討欠款的決心,也高估了自己。之後發生的幾件事,讓魏東亭徹底慌了神。
第一件事:老四胤禛成爲追討欠款的大臣。
老四是出了名的“冷面”王爺,辦事只講規矩,不講情面。如今老四接下了這個差事,別說他魏東亭的薄面不管用,就算是面對皇子貝勒,以老四的脾氣,也是照追不誤。
從這個角度來說,一個人能讓別人都怕,憑的還是爲人,地位、手段、權勢不過是錦上添花。就像太子,做人不行,做事更不行,所以站的再高,也不會讓人心生敬畏。

第二件事:田文鏡羞辱老狀元陳文盛。
欠款的官員們不敢跟老四硬頂,卻不代表不會在協同辦差的田文鏡面前拿架子、擺資曆。
只不過,田文鏡簡直是老四的翻版,只認理,不認人,手段態度比老四還強硬。
追討欠款的第一天,就毫不留情地當衆羞辱了老狀元陳文盛,一番誅心之論,差點沒把陳文盛當場氣過去。
這讓一同被傳喚的魏東亭,心有余悸,不得不放下姿態,表示會盡力籌錢還款。

第三件事:太子、老三相繼還款。
說情與擺資曆這兩條路都走不通,魏東亭便開始出昏招——攀比。
得知太子也欠了錢,且替太子借錢的人並沒有被田文鏡追債,魏東亭一改往日的怯弱,氣呼呼地跑到田文鏡跟前質問。
魏東亭此舉倒不是非要太子還錢,他只是想攀住太子這個“榜樣”,拖延還款一事。
沒成想,擔心事情被捅到康熙面前,太子轉頭賣了幾個官把錢還了,而老三胤祉也當衆將一張三十萬兩的銀票交給了老四。
這下,不僅攀比的對象沒了,魏東亭還被老四點名批評。
正是這三件事,讓魏東亭的態度,從最初的不以爲然,逐漸轉變爲壓力倍增。
隨後,魏東亭舍下臉面求到了老九胤禟處,被老九以沒幫老十爲由拒絕。爲了裝好人,老九又給魏東亭出了個主意,讓他去求老十三胤祥。

都說欠債還錢,天經地義。
話是這個話,理也是這個理。可事實是,道理向來只對“講道理”的人管用。
對于那些只圖榮華富貴,不求爲國爲民的官員來說,國庫有沒有錢不重要,反正他們得有錢花;百姓是否饑貧也不重要,反正他們吃飯必須得擺滿八碟十六個碗。
在這些人的眼中,欠錢是天經地義,還錢是強人所難,不還錢是理直氣壯。
這其中包括魏東亭嗎?
包括!
從表面上看,魏東亭比那些從國庫裏掏錢拿出去放貸的人強多了。
可究其本質,他們都一樣。都是只顧自己,不顧黎民社稷;都是拿著國庫的錢,吸著百姓的血,講著不是理的理,填飽了自己。

魏東亭登門拜訪的那一刻,老十三就知道對方是爲了欠款一事而來。
他本不想摻和其中,讓他四哥作難,奈何魏東亭是從小看他長大的老臣,他沒法將其拒之門外。于是,老十三禮待有加的將魏東亭請進了內堂。
一見面,簡單的寒暄之後,老十三就直奔主題:
“魏大人,您今天找我來肯定是有什麽事。”

只不過,魏東亭沒有接老十三的話,而是憶起了往昔:
“當年的光景好啊,老奴們跟著皇上收拾了吳三桂、耿精忠和尚可喜那幾個叛賊,又平定了邊境的幾個反王,天下太平,人心向上啊。記得老奴那時在乾清宮做一等侍衛的時候,有一天還背著你玩騎馬呐,你一泡尿撒在老奴的脖子上了。”

魏東亭的這段話,要分兩部分去看:
前一句是通過憶往昔,強調曾經的功績與付出——我魏東亭是爲朝廷拼過命的老臣,所以,無論我爲何而來,你都不能輕視我。
後一句則是在打感情牌,強調曾經的情分,讓老十三回憶起他的好,爲後續開口做鋪墊——我是看著你長大的人,情分匪淺,所以我要是遇到難處了,你一定不會袖手旁觀對吧?
老十三知道魏東亭的來意,自然也聽得懂魏東亭的話外音,他笑著回道:
“這事我記得,您來還教我們幾個阿哥練劍,背地裏還總是偷著多教我一招兩招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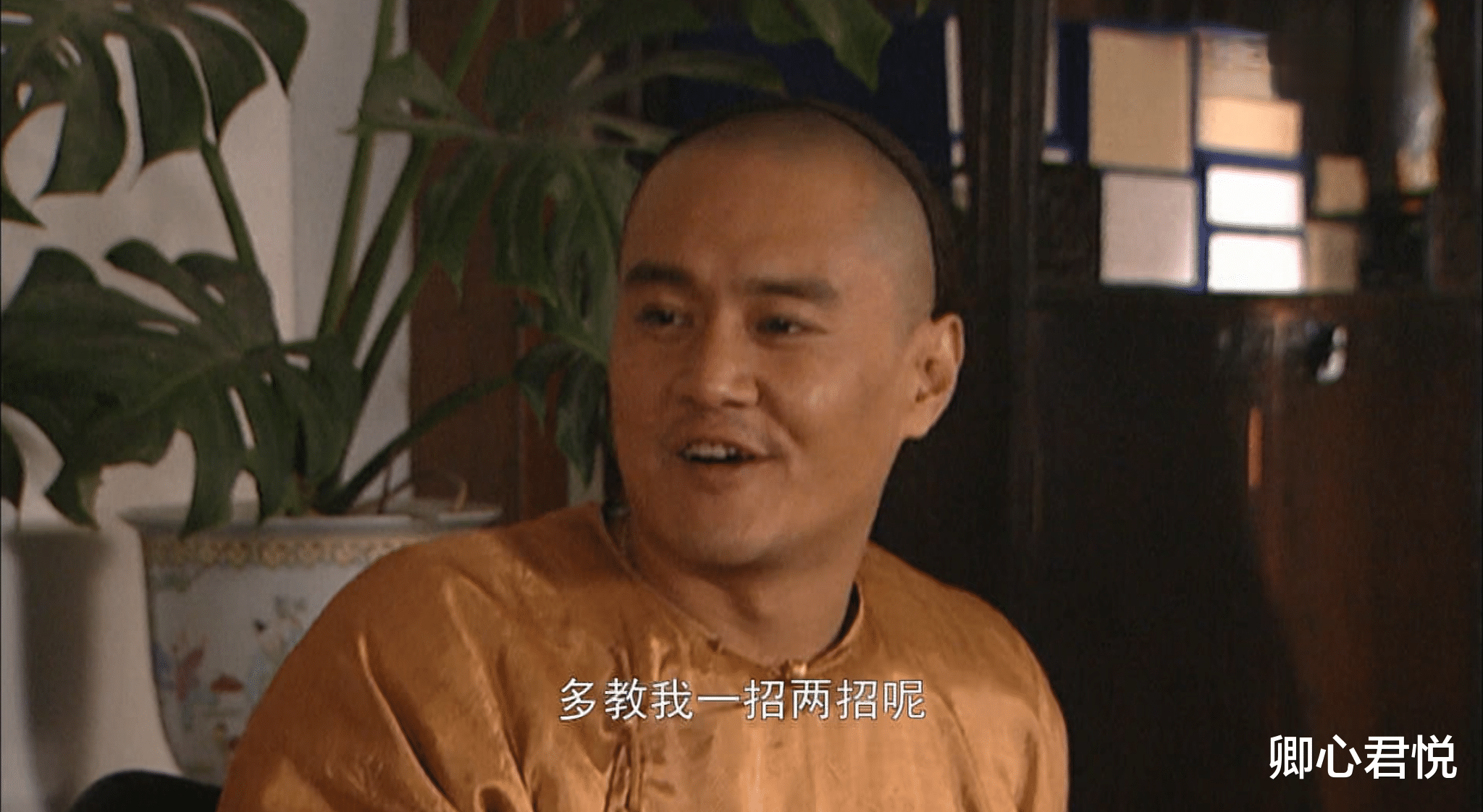
老十三的意思很明確:您老不用在這兒繞彎子了,您的好我都記得的,有事可以直說。
聽了老十三的話,魏東亭心裏有了些許底氣,不過他依舊沒有直接道明來意,而是繼續繞圈子。直到仗義的老十三主動送上台階,問他是不是遇到難處了,魏東亭這才點出正題:
“就是欠國庫的錢太多了,朝廷逼得又緊,四爺說過了十天不還清,就要抄家。”
只說難處,不提要求,這是魏東亭的精明之處。
對于魏東亭欠款的事,老十三自然有所耳聞,不過在他看來,這是康熙的旨意,是他四哥的差事,又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也因此,得知魏東亭欠款高達三十五萬兩,他略帶質疑的問道:
“我記得您在漕運總督任上的時候,好像也積了不少錢。您怎麽反倒落下這麽多虧空呢?”

到此,魏東亭明白,如果他不能給出一個合理的解釋,就算老十三念著舊情,也未必會出手幫他,于是他將欠款的“真相”悉數道明:
“十三爺,我有一句話只能跟你說,我的這些虧空多數都是因爲皇上落下的。”
“這事也只有皇上自己心裏清楚。皇上五次南巡,有兩次就住在老奴的家裏,我就是傾家蕩産,也絕不能讓他老人家有一丁點的委屈。可這兩次下來,我的一點兒積蓄就花光了,我就只有到戶部去借,幾年下來,就落下了這麽大的虧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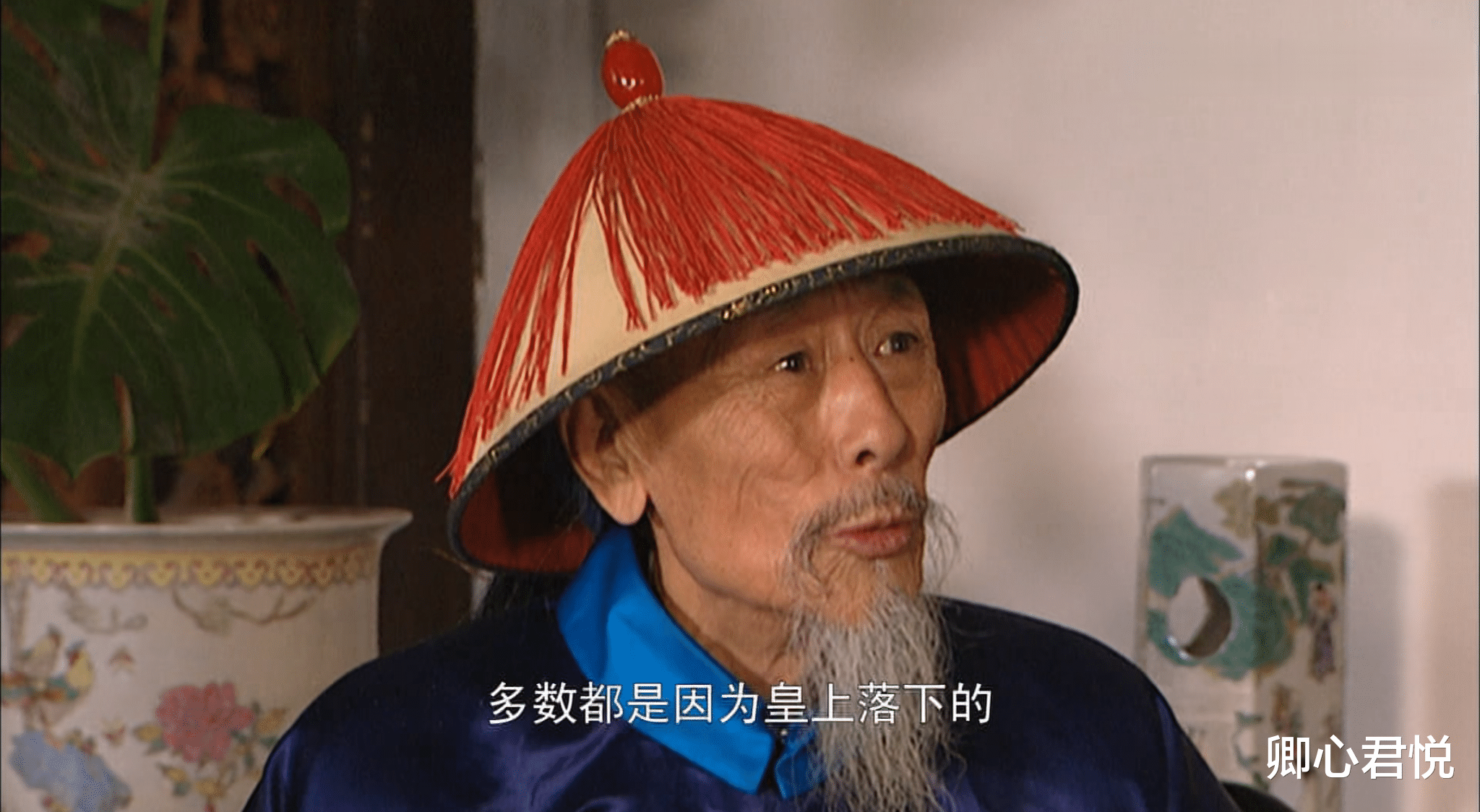
到這裏,我們需要思考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魏東亭的落空,真的是康熙導致的嗎?
不是!
注意魏東亭話裏的一個細節,康熙兩次住在他家,花的是他的積蓄,那三十五萬欠款,是之後幾年欠下的。
可能有人會說,如果不是康熙,他的積蓄不就留下了嘛,不就不用借款了嘛?
未必!
從劇中可以得知,魏東亭的兒子不到三十歲,就娶了四房妻妾,還在外面喝花酒、養妓女。光是給其中一個小妾打戒指,就花了五千兩。

可想而知,整個魏家的花銷有多大!
借錢度日還如此揮霍無度,要是有積蓄只會更甚!就算魏東亭的錢,沒花到康熙身上,他也未必會不去借款。
我們再注意一個細節:同樣是借錢維持家用,失了業的隆科多,只欠了3千兩,而沒退休依舊領著工資的魏東亭,卻欠了整整三十五萬兩。

這說明了什麽,就不用我多說了吧。
從某種角度來說,魏東亭屬于邬思道口中的第二類人——不安分而借之:
“這一類人往往是有資曆、有功勞,講排場、講闊氣的大官功臣。他們中哪一位不是從小就跟著皇上鞍前馬後熬出來的心腹重臣。”
所以,魏東亭說他的虧空是因爲康熙落下的,並不成立。

第二個問題:魏東亭花在康熙身上的錢,是怎麽來的?
康熙說,魏東亭爲他花費何止百萬。我們暫且就按一百萬兩算。
可要知道,一個四品京官一年的俸祿,是一百多兩銀子。魏東亭的官就算大一些,也不可能靠俸祿積下這麽錢。
也就是說,魏東亭在康熙身上花的錢,絕大多數都是爲官多年,尤其是任職漕運總督時,撈來的。要麽是民脂民膏,要麽是貪墨克扣,總之來路不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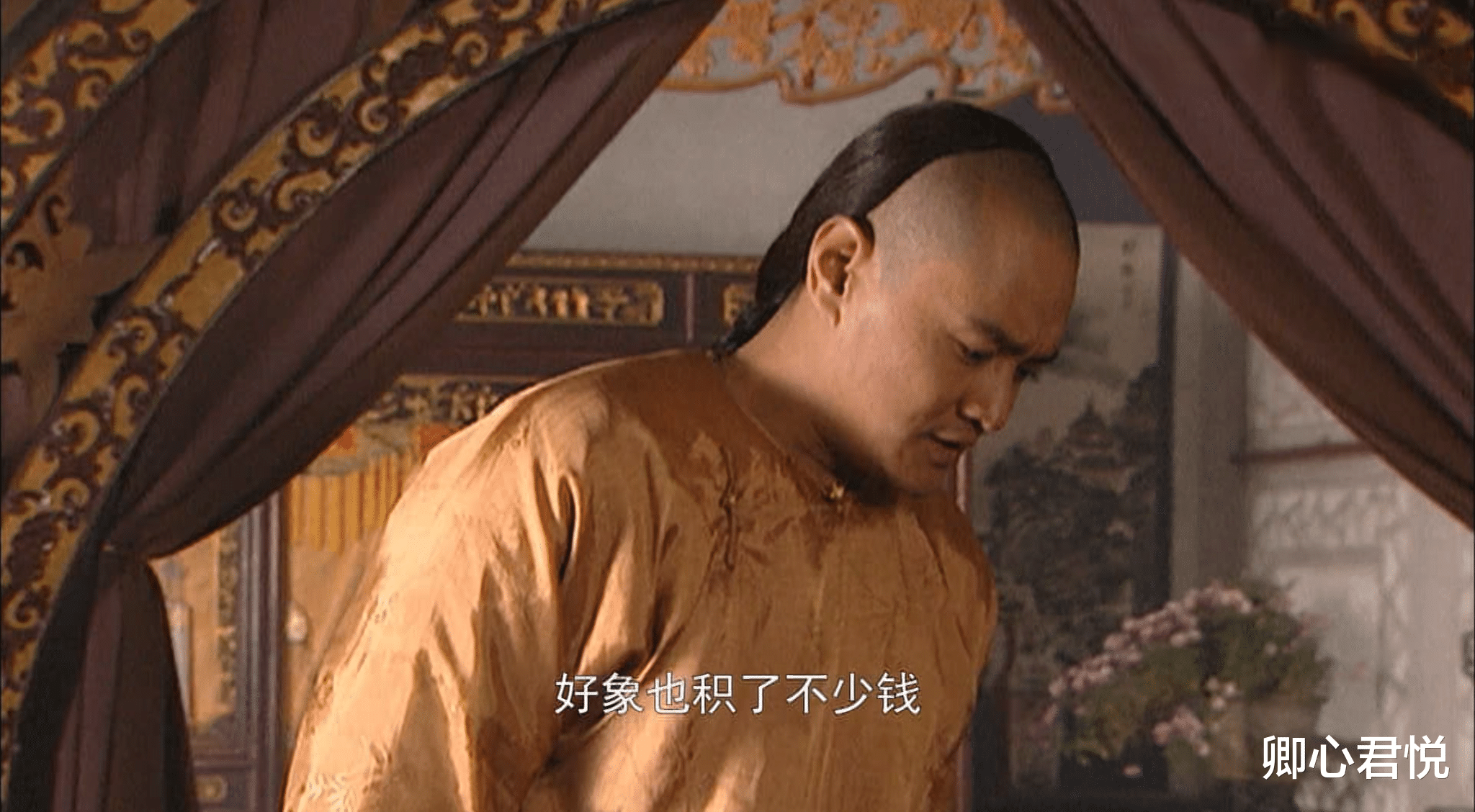
第三個問題:魏東亭斥巨資招待康熙是爲了什麽?
爲了向康熙表忠心,表孝心是一方面,但更多的是爲了討好康熙,進而做更大的官,撈更多的錢,過更奢靡的日子。
這才是康熙明知花了魏東亭不止百萬,事後卻沒主動補償他的原因,因爲康熙心裏明鏡一樣,魏東亭撈的錢,何止百萬。

而這也是我對魏東亭從同情,到無感的原因。
得知魏東亭的欠款與自己老爹有關,老十三立馬表示要去找老四說情。
只不過,老十三壓根沒見到老四,而最後的希望破滅了的魏東亭,當晚留下一封遺書,自缢身亡。
一條白绫背後的算計事實上,魏東亭甯願自缢,也不向康熙求助,不是他不想,而是一旦他開口,結局只會更慘。
理由有兩個:
其一,康熙並不欠魏東亭的。
上文提到過,魏東亭的錢並不是祖上的基業,是當官多年撈來的。他是把一部分錢花在康熙身上了,可這並不意味著康熙欠他的。
沒有康熙,他去哪裏加官進爵,貪墨斂財。就像劇中老四對欠款官員說的那樣:
“不錯,你們是爲朝廷出過力,立過功。可是朝廷也沒有負過你們,一個個頂戴花翎……你們當中誰敢站出來說一句,自己沒有吃過空額,扣過兵饷。”

在這種情況下,一旦魏東亭真的去找康熙求情,拿南巡的花銷說事,或是暗示康熙,他的欠款與康熙有關,康熙會怎麽想——
好啊,你撈錢的事我是睜一只閉一只眼。你可倒好,錢花光了,責任撇到我身上了,要算賬就把所有賬一起算了,包括你到底撈了多少……
即便康熙念著舊情,出手幫了魏東亭,那魏東亭與康熙的情分也就一筆勾銷了。
這種自絕于康熙的行爲,只會讓魏東亭晚年的生活更慘。賬是平了,可沒了康熙的恩寵,他以後的日子怎麽過?兒子的花銷從哪弄?

其二:擔責
找康熙求助,不僅可能會惹康熙不悅,魏東亭還可能面臨擔責的風險。
什麽責?
破壞追討國庫欠款一事的責任。
要知道,能跟康熙談舊情的,不止他魏東亭一個人。
一旦魏東亭開口,就等于直接把康熙推到了兩難的境地。不幫忙,容易背上置功臣、老臣于不顧的惡名;幫忙了,其他人勢必會攀比。
畢竟,幫了魏東亭,就得幫其他人,否則難以服衆。別說魏東亭情況特殊,在其他人看來,他們也給康熙拼過命,擋過刀呢。
最終的結果很可能是:康熙礙于情面,掏光體己錢,給所有跟他出生入死的老臣還賬。

可這樣一來,還追什麽欠款,還補什麽虧空。
到了那個時候,追討國庫欠款失敗的責任,勢必會落到魏東亭的頭上。而魏東亭也就成了康熙眼中那個不懂事,破壞大局的存在。
相對于向康熙求助,“以死清債”的方式雖決絕,但卻更有利。

一來,他的死,勢必會讓康熙內疚,進而一定會主動且心甘情願的幫他還債。既不用自絕于康熙,斷了君臣的情分,也避免了被抄家的結局。
二來,對子孫有利。
他的死,會讓他的家人得到照拂。只要康熙活著一天,他的家人就會一直處于康熙的庇護之下。這一點,從後續的劇情已經得到了驗證。

對此,魏東亭心知肚明,所以才會有他對老十三說的那句話:
“這法子,我使出來,連皇上都會幫我的。”
這是法子,更是權衡利弊之後的算計。
結語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魏東亭到底值不值得同情?
他不是什麽大奸大惡之人,更沒有像一些人那樣,拿國庫的錢去放貸,去謀私利。
可還是那句話,如果從本質出發,魏東亭其實與那些人無異。奢靡成性,揮霍無度,花的是國庫的錢,是百姓的血汗。
唯一的區別只在于,魏東亭把錢花光了,而一些人的錢還揣在兜裏。
這樣的人真的應該同情嗎?
寫到這裏,我想起了邬思道的那句話:“甘守清貧,他出來做官幹什麽?”

是啊!出仕爲官,又有幾人願意甘守清貧呢?
可出仕爲官,難道就該只爲一個“利”字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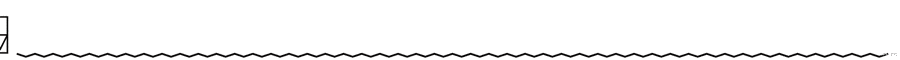
卿心君悅,讀別人的故事,過自己的日子。用文字溫暖你,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