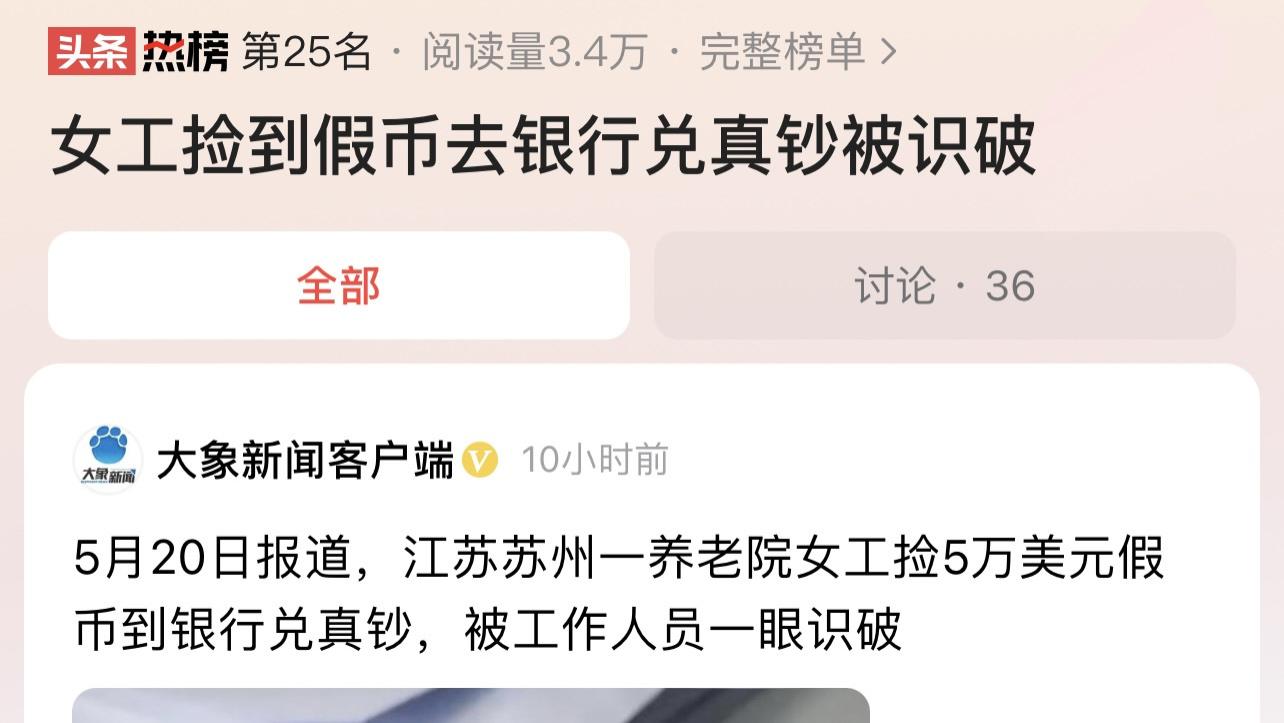新經濟形勢下,工業城市如何刷新存在感,走出一條柔性轉型路徑?改革與創新是必然之舉,對自身産業路徑的審視與蛻變亦很重要。國內城市中,工業三巨頭之一的蘇州堪稱産業平衡且“量轉質”效應最好的城市之一,近年來其産業結構均衡、産業效率提升。
對于工業城市而言,處于曆史廊道環境中的工業地段更新並非難事,說易行難的是如何實現産業“老傳統”轉爲“新優勢”。此時,深厚底蘊讓具有運輸、人才、區位等優勢的老牌工業城市重新重裝出發底氣更足,可以循著經濟演進的時間軸與世界産業布局的空間軸,找到自己在全球價值鏈上的新位置。

同質化競爭嚴重、傳統發展模式顯出頹態是諸多傳統工業城市所面臨的發展難題,一系列工業城市的成功範例表明,在堅守中漸變,于前瞻性規劃裏梯度布局,施行産業經濟與社會空間的雙重轉型,這樣的城市既有深厚的曆史底蘊,又不乏開拓精神與創新意識,發展方向明晰、步伐堅定,堪爲區域經濟發展中的中流砥柱。
從灰色到綠色
2014年,爲探索工業發展與節能減排相互促進、互利共贏的綠色轉型模式與路徑,工業和信息化部在全國篩選了一批重化工業特征明顯的城市啓動區域工業綠色轉型發展試點工作。湖北黃石、安徽銅陵、江西鷹潭、山西朔州、內蒙古包頭、遼甯鞍山、河南濟源、河北張家口、四川攀枝花、甘肅蘭州、江蘇鎮江等11個城市入選,力圖通過3-5年時間以多種舉措,在資源能源利用效率、汙染排放水平、工業結構調整等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在全國率先實現工業綠色轉型發展,探索建立具有推廣意義的轉型路徑和模式。

工業文明所特有的福特式大生産模式在城市規劃建設過程中面臨四大障礙:用大江大河的治理模式,來治理城市水系和給排水系統;用人工大規模造林的模式,來代替城市園林科學與藝術;用高速公路的交通模式,來規劃建設城市交通系統;用大工業流水線的辦法,來處理城市的各類廢棄物。此時,城市的發展思路應從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轉變。
早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遍及全球的大小工業城市就開始了從“灰色”轉向“綠色”的探索之舉,以跻身潮流國際旅遊目的地之舉迎來全新的春天。德國南部經濟中心慕尼黑成爲一邊是高科技工業與傳統農牧業,一邊是體育産業與音樂産業的代表城市之一。位居法國內陸的小型工業化城鎮維特雷則憑借傳統工業起家,在經濟危機中專注核心優勢並因地制宜向旅遊業轉型。果斷從鋼鐵、化學、煤炭等重化工業裏抽身轉向機器人、半導體、氫能汽車以及尖端環保科技等新興産業,日本城市北九州憑此成爲世界四大成功轉型的工業城市之一,僅以20年時間便從“世界環境危機城市”扭轉爲“全球環境500佳城市”。
這些城市的過往、現在與未來仍與工業息息相關,在工業基礎上發現並挖掘新的城市意義與特質是促進其轉型的必要前提。德國法蘭克福展覽會門口有著一座21米高的工人雕像,其創作者藝術家波洛夫斯基表示,“我希望借此感謝那些辛勤的工人們,他們夜以繼日地工作,爲這座城市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人類的生産工具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並改變著制造業的未來,城市也是如此。城市的“工業景觀”正在漸漸地凸顯工業遺産的價值,由單一走向多元,由個體走向整體。比如,利用交通樞紐優勢,打造特色休閑旅遊,曾以“世界工廠”著稱英國城市伯明翰優勢明顯,更爲難得的是,其不僅考慮經濟轉型,同時將城市文化建設作爲轉型的重要內容。
從高碳到低碳
第二産業的新生是吸納就業人口的重要途徑,亦是高新技術發展的堅實基礎。向工業化時代告別,壓力巨大,挑戰衆多,但具有遠見的工業城市明晰這樣的必然轉變,從而堅定的以傳統産業改造優化原有生産力,又以新興産業爲發展積聚新動能。
被稱爲“世界鋼鐵之都”的匹茲堡曾是美國最著名的工業城市之一,一度有美國鋼鐵公司、西屋電氣公司等21家美國500強公司將總部設在匹茲堡。但與汽車之城底特律轉型不及驟然黯淡不同,匹茲堡早早開始研究轉型之策,改變城市産業布局。時任市長理查德·卡利久裏表示:“我們要成爲世界主要的研究之城,也要成爲服務與零售、健康護理、器官移植之城,以及高科技之城。”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精密科技工業與軟件工程隨即成爲匹茲堡的産業攻關重點。當地人談到匹茲堡的轉型時充滿自豪:“從前,我們擁有煉鋼廠和灰色的天空。而今天的匹茲堡以教育中心、醫療中心聞名,人們不再通過昔日無比輝煌的鋼鐵工業來了解這座城市。這是一座新的城市,新的匹茲堡。”

在世人印象裏,蘇州“軟硬皆可”,江南水鄉、文化名城的清新感一直在線,是著名旅遊城市,同時蘇州又是地道的工業城市,制造業、代工業發達,蘇州工業園是全國産業園區建設中的翹楚,兩種形態的蘇州奇妙的沒有絲毫違和感。
2010年時由紡織、鋼鐵、機械與各種代工企業撐起的傳統産業還占據了蘇州規模以上工業比重的72%,新興産業僅占28%,彼時以全國0.09%的國土面積創造全國2.1%的GDP,蘇州的土地開發強度早已觸到天花板。
但到了2016年,前者占比降爲50.2%,後者上升至49.8%,並在隨後一年後者完成對前者的反超,蘇州經濟實現新舊動能轉換。讓蘇州産業烙上“新”“輕”“高”關鍵要素的是,其堅守實體經濟,助推高成長性産業集群集聚,著力精細增長,以預見性布局新興産業爲轉型謀得新空間。連續多年蘇州新興産業投資占工業投資比重超過60%,以新能源、生物技術和新醫藥、高端裝備制造爲代表的高技術、高附加值産業成爲引領蘇州經濟發展和産業升級的主力。
瑞士城市巴塞爾繁華非常,但讓人訝異的是,萊茵河兩岸多的是大型制藥公司。羅氏和諾華這樣的醫藥界巨頭就在大量銀行和保險公司之間安然從事研發和生産工作。不過,這樣的情形畢竟還是個例,經濟學家認爲城市發展有其固有模式:大部分城市圍繞工業興起,取得成功後城市擴容,規模較大的工業生産活動日漸遷離到了城市邊緣,唯有小型工坊和新興經濟體散布在城市內部,形成一個複雜的産業網絡。

《經濟學人》撰文指出:“制造業數字化的步伐加快,使得人類改造世界的方式正發生前所未有的變化。很多海外工廠逐漸搬回到發達國家。”但不限于發達國家,工業城市想要做到經濟再平衡並不容易,大都市和很多工業城市都在調整其工業基礎設施的規劃,動辄數百公頃的工業用地的調整對于任何一座城市而言都不是易事。更進一步的解讀是,城市紋理正變得更加細密化,留給制造業的空間日顯狹窄,大型工業很多時候不再身處城市核心地帶,它們的空缺被新型工業空間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