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城中之城》劇本策劃 夏心愉
首發 | 秦朔朋友圈
結緣《城中之城》制片團隊是在2020年,說來那還真算是一次“秦朔朋友圈”的線下奔現。
我在秦朔老師的引薦下來到興格傳媒,知道了在這裏將完成一次“從零到一”的嘗試:制作一部關于現代金融業的現實主義作品,銀行業首部行業劇。
興格傳媒董事長楊文紅的一句話說出了整個團隊的興奮點:現實主義作品,其實是透過一個個劇中人物微觀主體的命運,折射出一個大時代,“這是新聞人出身的主創團隊所難以抗拒的”。
還記得在那些劇本討論會上,對應著戴其業、趙輝、苗徹、蘇見仁、陶無忌等這些“目標人物”的塑造,我把自己筆下曾經觀察記錄過的銀行從業人員,領軍的將帥或是平凡的基層奮鬥者,都一一“對號入座”,講他們的故事、業務,和他們的用語、金句,供編劇老師選取采用。

我總覺得,這些真實存在過的人和事,即便被戲劇化處理成了一些片段或細節,也一定會激發共情,在某一個人物、某一句台詞、某一次人生抉擇,把同在一片金融江湖的觀衆,接應而來,把2016~2019年的那段金融業創新尋路與合規發展,重走一遍。
那一刻我在想,原著中對于戴、趙、陶三代師徒的“時光之沙”隱喻,何嘗不是在今天,《城中之城》捧給觀衆的“時光之沙”。
我有一名在銀行做合規的讀者,看完劇通過 “愉見財經”後台聯系我,說劇中涉及的大資管時代其實也恰恰是合規工作“專業主義”大顯身手的時代,站位靠前賦能一線,需要他們把前台業務沖動之下“容易但不合規的路”糾偏成“有些艱難但合規的路”。
他不無自豪地說,自己或許曾經救下過我們筆下的戴行長。
還有一名觀衆把自己代入了劇中的趙輝, 同在領導崗位上面臨是非功過評價的他,責問我們爲什麽不能給趙輝式的幹部多爭取一些“灰度容忍”,保全一個男人的驕傲, 和推動銀行發展的一員猛將。
另有一個朋友看完劇後要拉我去喝一杯,是因爲,他在故事裏看到了當年的那個,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的、年輕又熱血的自己。
說來也許巧合的是,在劇本創作勞動密集的2020~2022年,我們對劇中寄以了理想主義色彩的陶無忌一角,所賦予的工作幾乎覆蓋了創作結束一年後才被提出的“五篇大文章”金融大方向;
而當時在豐滿趙輝人物形象時,我腦海裏反複出現和對標的某行領導,到電視劇播出時,卻也走了和趙輝終局相似的人生命運。
從“九正一邪”看人性
在劇中,只出現了一集就領了盒飯的戴行長,卻恰恰是我個人在創作時投入感情和思考最多的角色, 並將這一思考延續給了趙輝和陶無忌。
編劇老師采納了我給戴行長寫的兩句台詞,一是 “九正一邪”,二是“現在被認可的創新,在一開始的時候,不都比監管多走了半步嗎”。

這條 “九正一邪”的線索,輔助了“白襯衫”隱喻的主線索交叉鋪陳,幾乎貫穿了全劇。
編劇團隊當時在塑造人物時想要達成的,正是這種關于人性的複雜思考,它不是非黑即白,它和光同塵,是以一個“掌握著資金及金融資源分配”、在大衆眼睛裏“離錢最近”的行業爲顯影劑、放大鏡,去敞視人心的圍城, 敞視 那些可能的職業理想與榮光,欲望與野心,驕傲與不甘,以及衆生同樣都在面對的七情與六欲,親情、愛情、兄弟情。
戴行是一個怎樣的金融人?全劇其實借著幾個角色的口都問過這個問題,但是並沒有留下定論。我們讓大家明白戴行的操作是違規的,但較之付以更多筆墨的,是徒弟、後輩們對戴行不變的尊重與懷念,以及對一代老銀行家敬業精神的傳承,名譽聲譽的保護。
說回到劇情中,戴行首先是有作爲、敢擔當的,這恰恰是身居要職的領導最寶貴的品質之一。他本可以不幫嘉祥,作爲分行一把手,戴行手上有大把戰略客戶、大客戶,完全沒必要爲了一家民企的需求而費周章。
但是戴行依然選擇去幫這家他扶持了十幾年的企業,去保護民族産業,去抵禦資本市場做空力量。
但這筆資金的流向仍然是有問題的,因此只好采取變通,“表內不行走表外”。
這類操作方式,以表外資金通過一或多個資管通道進行輸血,以“優先-劣後”的結構化設計或輔以“借款企業股權質押”等方式來控制風險,最終投向表內資金不可及、或不便及的標的或領域,在2016年前後的資管大發展時期,並不鮮見。
當年紅極一時的“寶萬之爭”背後,資本市場的酣戰裏,就有著銀行表外資金的參與。現實中如果當年有“戴行”,不失爲金融創新弄潮兒。
然而,放到資管新規、監管穿透後的今天來看,這樣的做法是踩線的。戴行的操作,盡管幫了企業,但過程中仍然是置表外資金于相對較高的風險。所以編劇讓戴行最後倒在了“九正一邪”的那“一邪”裏。
然而從另一方面來說,戴行又是作爲的。編劇老師巧妙地用蘇見仁罵趙輝的一句話,抛給觀衆一道思考題。蘇見仁說:“你要想白襯衫一輩子一塵不染,那你除非是阿Q,你永遠呆在底層,你什麽事都不要做好了。”

我們身邊其實也有一種公司領導,對于要擔責任的決策,就開始當不倒翁,請示彙報拖拖拉拉,事成不成不重要,追責不在自己頭上最重要;
或者還有另一種人,到了某個中層的位置, 就不再想著往上了, 不是缺乏抱負心, 而是在 爾虞我詐裏滾成熟了,知道再往上風險變大了,欲望抵不過求穩,熱血方剛終究抵不過精致利己。
順著這條線索,趙輝是全劇最完整繼承戴行事業品格的角色,並且在角色完成上, 他同時繼承了對 “九正一邪”的思考與爭議。
其實撥開人心看,趙輝的底色是正直的、自律的,更重要的,是驕傲的。 要這樣的人去像蘇見仁一樣可以隨手貪、隨手收名表,是不可能的,這根本不是 “能不能貪、敢不敢貪”的問題,而是,這個驕傲的人根本不屑于貪。
但是,苦了各位觀衆一顆隨著趙輝命運起起伏伏的心的是,爲了反腐大劇欲揚先抑情節的完成, “氣人的”編劇團隊只能讓趙輝就範啊。
其實我們在最初搭建人物架構的時候,曾經把可以腐化一個領導的“要素”都擺在台面上探討: 錢財、美色,太低級,在趙輝面前根本無足輕重,甚至近乎羞辱,自律的他未必正眼看一眼; 孩子的健康、對前妻的思戀,這些最能觸及柔軟內心的情感與家庭責任,可以讓趙輝難過,但仍然不足以讓他動搖。
真正撼動一個驕傲的人的,是擊潰他的驕傲。 是讓會徇私舞弊、會交 “投名狀”的小人得志,讓自己恰恰潰敗在清正的、不同流合汙的驕傲裏; 之後再補一刀,小人當上自己頂頭上司後第一件事,就是蠶食瓜分自己職業高光點的業務項目,閹割掉自己最後的驕傲。
所以,從原著到編劇改編,寫給趙輝的,根本不是普通的基于人性貪欲的那些利益圍獵、爭權奪利,而是一個恰恰幹淨清高的男人,在現實的泥潭裏,精神世界信仰的崩塌。
《城中之城》第十集,上大分的節奏感BGM猶如戰鼓起,背景音樂裏仿佛呐喊的人聲,卻聲畫對位著面無表情的、沉默的趙輝,開車突然一把急轉掉頭。這是一個男人心被寒得透徹的樣子。

從這集開始,趙輝換襯衫了,由白變成偶爾的黑(呼應白襯衫隱喻),他的職場與內心開始有了正與邪的拉鋸。
但是,抛開現象看趙輝之後的本心,你會發現,他一直都沒有爲權、爲錢。 他出發的第一步,只爲了撥亂反正,拾回本就該屬于自己的驕傲,同時作爲一個活生生的人、一座壓抑自己已久的 火山 , 他猶猶豫豫地、進進退退地,縱容了自己內心最軟肋之處(孩子、戀人)的安頓;
而再之後,趙輝其實是上了賊船一直在找路子下來,內心的天平從來都是往 “秉公”傾斜,只不過要兼顧全身而退的可能性;
最後,當他發現自己已無路可退時,相比陶無忌一直在外圍找突破,趙輝才是那個親身在局者,並親手自殺式引爆了核彈,解決了壞蛋、幹掉了大 BOSS 。
只遺憾,在這個自己設計的局裏,同時湮滅的,還有他自己。
這裏補充一句,大家有沒有發現,其實最後幹掉兩組大 BOSS 、即吳家父子和沈婧的,恰恰是兩個亦正亦邪的親身在局者: 趙輝與田曉慧。他們以自殺式引爆的方式,完成了“正義的勝利”,也完成了灰度角色 對自我的救贖。
要問在這座“城中城”、這個“局中局”裏趙輝的“九正一邪”,我同樣寫了一句詞給他,在他解答陶無忌的困惑時被說起:“能通便是法,能立便是地,能伴方爲侶,能克方爲財”。
他的“九正一邪”何嘗不是和戴行長一樣,試圖在艱難阻滯中找一扇變通法門,給自己的理想找一個立身之地,讓一切重歸有序呢?
“九正一邪”的探討,最後接棒到了陶無忌的手上。大家會發現這個人物也不是一根筋的,從最初上櫃台,他就是一個有小心思小欲望會在洗手間堵領導的人,到做衡慧公司貸款時也會選擇性忽略對方受托支付的問題和共債的風險,一門心思要搞定項目,再到後期下分行做審計時靠弄傷自己來解圍的小動作,陶無忌其實一直有“邪”的那一面,這個“邪”其實師承了趙輝,他也在用變通法門,只不過畢竟職場經驗還淺,這些變通方法看起來也還過于稚嫩,更偏苗徹對他的評價:“雞賊”。

但是,陶無忌又是有成長的。(有些觀衆覺得陶無忌在劇中開始和結尾時人格不一致,其實這是編劇想體現的人物成長。)
比如,從一開始對趙輝的崇拜,更多的是光環崇拜,陶無忌是明顯有一己私欲的(當然這對年輕人來說也很真實、很正常),他想賺錢買房,也升職加薪,他想建功立業;
到後來對苗徹的崇拜,已經開始和光環脫鈎,甚至和世俗意義的個人得失也逐漸脫鈎,轉而開始一種對“金融正心”信仰的遵循。同樣的,他一開始的小聰明,更多像“耍滑頭”,目的是爲了成個事、邀個功、表現自己和證明自己;
後期的小聰明,則開始有了像他的師父、師公那樣的開合,他開始不那麽在意自己升不升職、能不能符合女友對賺大錢的期待,他甚至有了苗徹的那股勇——哪怕砸飯碗,也要幹到底,只是,恰恰爲了把事兒做成,得找一些變通法門。
從“富貴”與“善終”能否兼得看人性
我的家人不在金融業內,他們在追完劇後,提出了一個偏頗卻值得思考的問題: 爲什麽劇中類似于吳顯龍這樣的人,那麽有錢了,結局還是不好,那人要賺那麽多錢幹什麽?
下文進入從《城中之城》探討人性的第二個角度,以劇中吳顯龍、或是謝致遠的人生,去折射真實財經世界的大佬沉浮錄,爲什麽 “富貴”與“善終”,很多時候在他們身上難以兩全呢?
我用吳顯龍的資金運作,體現出的原因一,是錯綜的資金鏈條,厘不清也退不出。
各位看地産商,可不能像田曉慧看小吳總,只見金玉其外。 我想說的是,在看明白真實資産負債表的 “負債”項前,不要爲那些“資産”鼓掌,在看明白杠杆撬起的風險前,不要爲眼前的收益喝彩。 當我們從局外看到吳顯龍那樣的集團化運作資産很厚,但其實借陶無忌的審計之眼厘清來看,裏面全是短長資金騰挪: 一堆資産拉久期,一堆債務在生息。
再深究一步,原因二,是錯綜的利益捆綁,牌桌上沒有人能擅自半途起身。
在原因一之中,我們還只是從一個大佬和他背後的一個集團 ——如此單一視角來看資産負債謎團的。 但其實讓大佬無法全身而退的,還遠不止于此。 更深層次的原因是: 在一個圈層的謎團中,在資本與商業的謎團中,在政商旋轉門的謎團中,利益還是深度捆綁的。
換言之,你一家的命運,已經深度捆綁了很多家的命運。 就像謝致遠,他纏上趙輝是因爲他也身不由己、抽不了身,劇中的穆總顯然是一個與他有深切利益捆綁的人,謝致遠如果撂挑子,穆是不會善罷甘休的。
現實之中,我舉一個某大和某融兩個集團及其旗下控制的金融平台之間的 “協同”運作,就可見一斑: 某大人壽通過購買某商辦資産,向某融旗下的某天金融投了 19 億,而某融人壽通過一只私募,又向某大地産投了 15 億; 某大人壽通過 A 信托通道資管計劃,投向某融旗下某天城投項目 10 多個億,某融人壽又通過某信托通道,投向某大一中西部省會城市項目數億元……
如此這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就是一夥人的利益關聯,身家前路、乃至個人及家庭安危的緊密捆綁。 到了這一步,像不像劇中的謝致遠,你看他開個豪車,調度資源能力一流,猶如過河卒子,能潇灑地橫著走。 但是,回頭已無岸,身不由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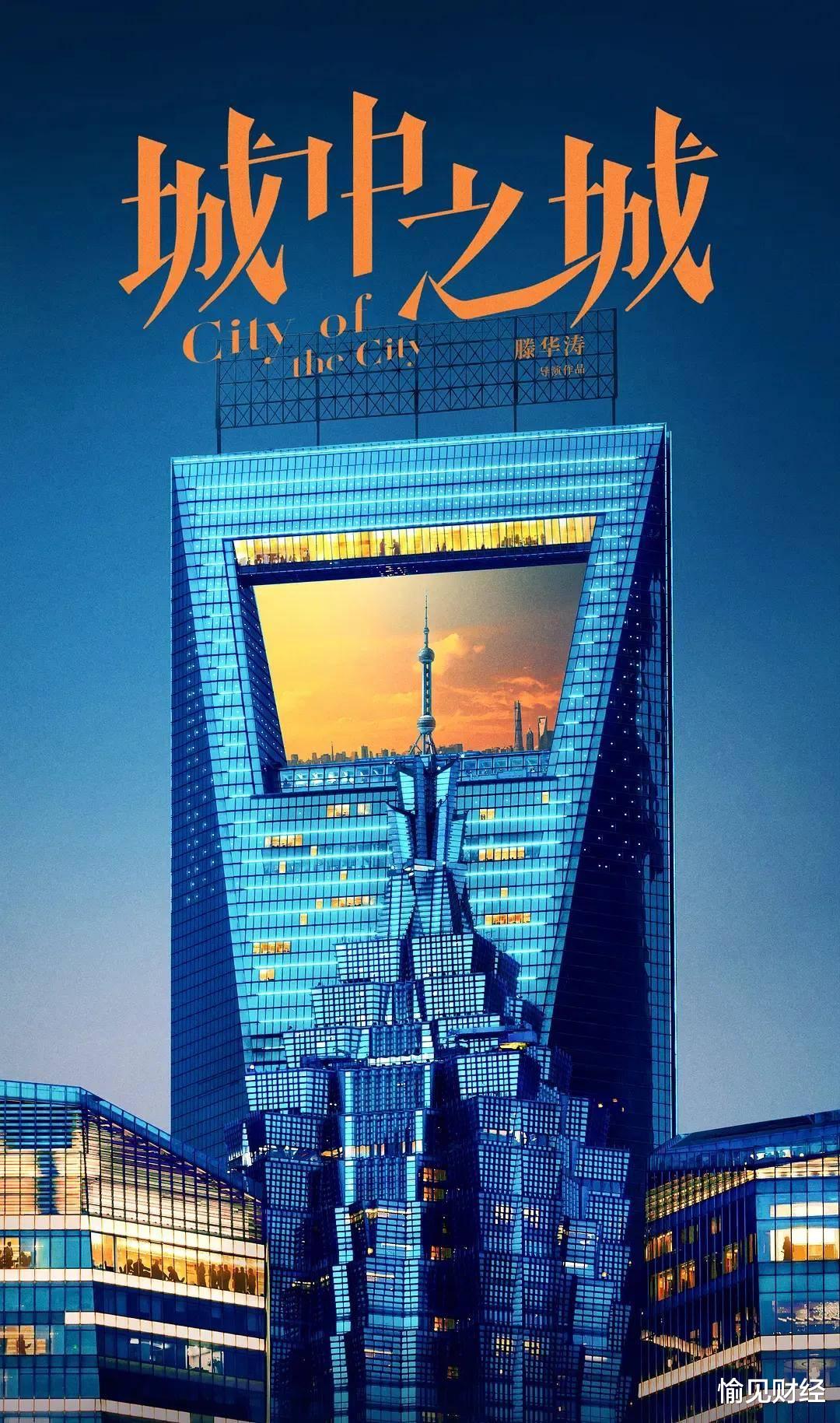
原因三,周期的覆滅,與大象難以轉身的笨重。
我們不妨回到起點來倒問,一個人,到底要如何獲得巨大的成功,乃至締 造出一個商業帝國? 這背後必然離不開三個要素:一是發展到一定階段後的外部 “合作關系”深度捆綁; 二是在上行周期敢于拉滿杠杆,急速做大; 三是,噴薄的欲望和野心。
我們先來說“拉滿杠杆”。在《城中之城》,無論是對駿龍集團資金運作的高階版、還是對田曉慧母親炒股的平民版,其實我們都探討了高杠杆的“雙刃劍”。 對于前者而言,在上行周期滿目繁華下,擲下的那一把大杠杆,到了下行周期,就轉而變成了誘火焚身的導火索。 君不見每一輪民營經濟的病來如山倒,都是從杠杆最高的地方開始坍塌的嘛?
以地産行業爲例,從原理上來說,拉滿杠杆做大做強的底層邏輯,必須有兩樣東西持續支撐:
一是資産價格只能上不能下;
二是貨幣周期只能寬不能緊。
這兩樣東西如果動了,那麽高杠杆模式就無以爲繼。 而《城中之城》所表現的 2016~2019 年的故事,正值周期的切換,從深茂行逐漸收緊的信貸政策、 到 對地産商越發嚴格的 “名單制管理”,以及表外融資渠道的步步收嚴, 都 是壓倒駿龍集團、推動情節發展的重要外部因素。
原因四,是欲望的剛性,與英雄身退的落寞。
其實我在過往的很多文章裏表達過一個意思,有點像劇中蘇見仁的生活方式: 如果只從單個人、單個家庭純粹的生活質量來看,對很多人來說,比較基本的財務自由並不是一件多難的事兒,到了這一刻對上述利益鏈條其實還浸淫不深,也基本還是可以收手的,中富即安,反而是生活質量抛物線的最高點。 江湖止、人生始,約上好友高球打打,泡壺 好 茶悠遊物外,還有時間參與兒女的成長 ……這些,其實反而是轉身再回江湖厮殺的那個選項裏,需要放棄的。
那是什麽,讓人放棄了個人生活質量登頂的惬意,轉身去拼更大的江山呢? 不排除這中間有一批人,動力源來自某些公共利益、社群利益,上至爲行業尋路,商業報國、科研報國,下至爲了公司這幾百上千號兄弟,再謀一條更長遠的發展道路。
但對余下的人而言,其實就是一把欲望與野心,他們要的早不再是錢這個俗物,他們要更大的 “成功”,更大的城池,更大的威望或影響力,每上一個圈層,都要出這個圈層的頭地。
而欲望這個東西,是剛性的,一旦嘗到過大成功的甜頭、和因此帶來的那種衆星捧月一呼百應的威望,要從中“事了拂袖去、深藏功與名”,對那些野心和事業心勃發的人來說,是非常困難的。
講兩個我身邊相對熟悉的大佬的案例。
其一。 十幾年披星戴月,終于到了深交所敲鑼的那一天,大佬說身體快累垮,反正公司成了,對得起股東對得起團隊了,自己也想退幕後歇一歇了。 但話音才落沒幾天,馬上上市的消息一傳開,拉他去起投資板塊的機會來了,拉他借分公司擴張名義到招商熱情的地市搞塊地的機會來了,拉他再做一家同系統內公司的大資本也來了,甚至連撮合兒女親家大資源的路子都來了。
好一番花團錦簇。 于是沒過多久,大佬就把自己說過的“功成身退”計劃抛在腦後了,轉而又去熱熱騰騰忙乎下一件事兒了,還跟我說,這個上市公司才幾十億,太小了,以他的能力和已經走過一遭IPO的資源積累,未來至少要搞個千億級的。
人間終非修仙地,誰能在這一個個活生生的機會面前,一句句擡捧之間,一個個更大的願景面前,說走就走了呢?
其二。 另一位非銀金融機構高管,倒是退出江湖了一兩年,只不過原因並非主動,而是受制于一場敗北的宮鬥,又逢他原來深耕的那個非銀板塊機會收縮,說是心有靜氣閑雲野鶴,其實只不過是沒有太中意的下家。
在那一年多裏,他比過往任何一個時候都更樂意召見我們這種後輩,我們甚至還有了能登門拜訪的機會,只不過每次都要貢獻巨量崇拜情緒價值,聽他把過往種種輝煌一一道來,經驗一一教導,免不了還有不少重複信息。
對這樣的大佬,我頗覺有點殺手锏的一句哄,便是“哎呀您的格局您的經驗足以寫好幾本書,我要有機會參與下一個電視劇一定以您爲原型”。 這句話總是很受用。
一個事業心勃發的男人需要的人生路徑是什麽呢?立身、立業、建功、留名、指點江山、改變行業。
有次在拜訪完大佬回家的路上,我和一個同伴感慨: “英雄身退的落寞堪比美人遲暮”,不到一定境界,耐不住此等“奈何花落去”。 果不其然,終于一段時間之後,一個頗有名氣的集團金融板塊老總的位子騰了出來找上了這位大佬,他披挂再上陣。
說這兩個例子,無褒無貶無任何價值判斷,畢竟“雄心”和“野心”、“願望”和“欲望”僅一字之差,真正有沒有發心,只有大佬本人最明白,而我們這些吃瓜看劇觀衆,無非是從一個終局來倒推,來做事後諸葛亮的評價。 如同評價吳顯龍或是謝致遠,成王敗寇。
只是回到原點,扣回主題,也扣回《城中之城》在設計人物命運時所遵循的因果關系,“九正一邪”是否必然通往衰敗? 打造江山是該見好就收還是該不斷擴張? 這些本身或許都是僞命題,而真正有價值的卻是:
一看發心,爲何而戰;
二看擇途,滄桑正道;
三看節奏,攻守有節;
四看做人,厚德載物。
《城中之城》大結局上演,在參與劇本創作的過程中,看著劇中人物唏噓的終局,我自己反思的一個問題是,人生啊,最後結出的果子該是“五福”,切莫爲了其中的某一福,就枉然耗盡了余下福報; 顛倒妄想江湖路,笑一時並不難求,最後的功過評價還是看他是否善終,笑到最後才是有本事。
《城中之城》裏,有人锒铛入獄,有人如履薄冰,有人笑到最後。歡迎你一起追劇,品評人生。
